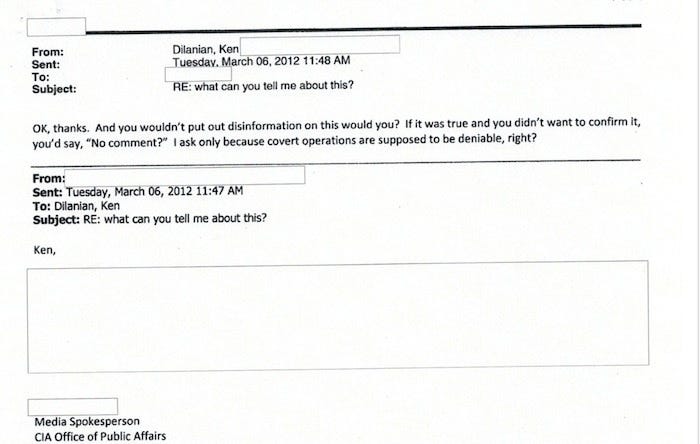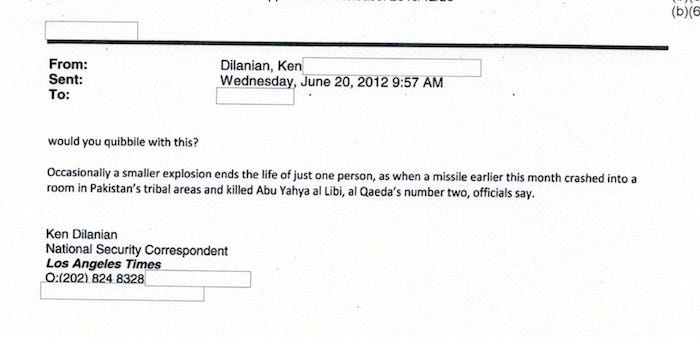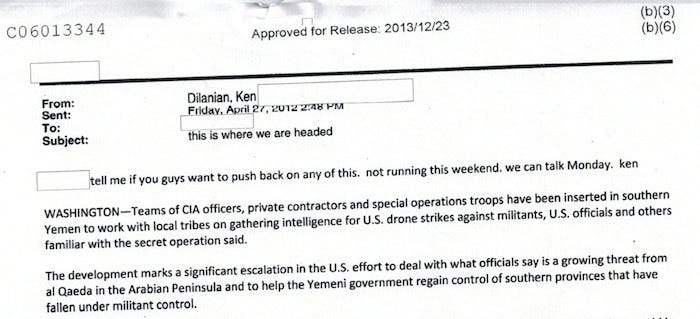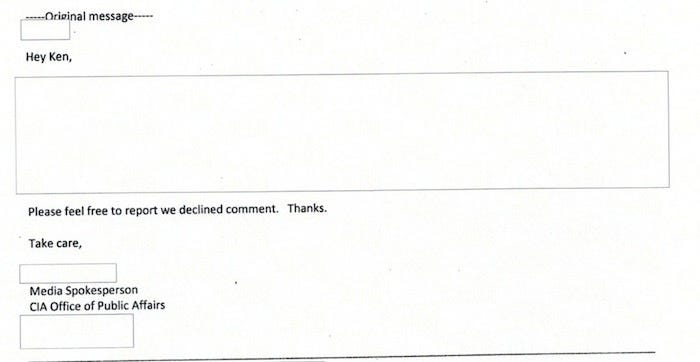资本主义哈巴狗很喜欢宣传非暴力,怕的就是他们的财产受损。印度这种独立之后还保持对英国女王忠诚的,是他们的宣传榜样,而刚果的卢蒙巴这种要把本国资源收归国有的,基本都被他们暴力做掉了。
现代战争基本上光是有枪也没胜算,除非能把正规军争取过来,所以非暴力革命变多是客观条件改变的结果,而不是想要非暴力革命的人变多。
即使是社会党国际这种被改良派影响很大的社会主义分支,都明确认同暴力反抗暴政的权利,反倒是中国反贼中类似刘晓波的傻冒太多了。
而马克思支持暴力革命更不奇怪,人民当然有暴力革命的权利,更别说当时根本没有非暴力革命这东西,刘晓波这种完全排斥暴力的设想实际上是根本行不通的,即使是现代非暴力革命,很多时候都有暴力伴随。
列宁的先锋队独裁理论,是起源于布朗基的,而不是马克思,马克思是反对布朗基那套的。
资本主义在今天,和马克思年代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硬套马克思主义,自然今天的很多现实都解释不了,但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本质,还是成立的。
马克思当时针对的是纯粹资本主义,而在全球南方,纯粹资本主义的确造成了绝对贫困,而欧美的社会主义者的战斗使得资本主义不再纯粹,资本家被迫把部分利润吐出来,所以马克思的预言就失效了。
是的,所以请你这条资本主义哈巴狗不要再号称自己支持性少数平权了,因为最早为LGBT说话的是你最讨厌的社会主义者倍倍尔;也别鼓吹什么住民自决了,最早明确提出民族自决概念的是你恨得要死的列宁;也别说自己支持全民医疗了,英国的医疗系统是你讨厌的左疯工党铸造的。还有,也别再号称无国界主义者了,最早喊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是你的死敌马克思,最早主张废除死刑的还是马克思,最早支持普选权的,对不起,还是马克思,哈哈哈哈。
哈耶克那那本破书,内容就两个:1,把社会主义等同于中央计划经济稻草人;2,诅咒福利国家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这个纳粹,是明确反福利的,所以才当了铅笔社祖师爷。
瑞典社会民主党受拉萨尔和伯恩斯坦的影响较多,但这两位也并未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只是认为资本主义可以自然演化到社会主义而已,呵呵。支持自由市场的当然是纳粹了,瑞典的教育医疗住房养老这些都是国有化的,可不是你亲爱的自由市场,更不会像你这个傻逼一样主张把水资源私有化,呵呵。实际上福利国家就是起源于马克思的理论主张,所以可以说认可福利国家就认可了部分马克思主义。
对不起,北欧模式本身并非社会主义,但是更不是你亲爱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然滚去解释一下为什么瑞典政府要禁止炒房?
右派们既然那么喜欢护着极右纳粹,那就滚去死在他们的怀里算了,不知死之前会不会后悔之前养虎为患呢?宽容这种屁话和极右纳粹们去讲,不要和社会主义者去讲,知道吗?
比利时根本就不是北欧,傻逼极右纳粹们又开始树稻草人了?可笑,实际上比利时是殖民帝国之一,当年瓜分非洲的时候害死了1500万刚果人,后来还设计害死刚果首位民选总统卢蒙巴,这国家的历史肮脏度堪比大英帝国。而北欧国家除了一千年前的维京海盗时代,近代并无对外殖民历史。
原教旨主义者除了法律禁止仇恨言论之外,其他没什么迅速有效的办法,只能坚持政教分离,提供高质量免费教育,把原教旨主义斩断。同时,原教旨主义和新纳粹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欧洲政府一边连罩袍都要禁止,一边却由着极右纳粹泛滥,那么就别想根除原教旨主义了。当然,为什么政府会如此,是另一个问题了。
在巴列维之前,伊朗民选首相莫撒啊德是支持政教分离的,但就因为主张将伊朗石油国有化,就被英美政府联合推翻,然后换巴列维这个傀儡上台。巴列维时代,除了新自由主义之外,美国人在伊朗是有特权的,美国人犯罪没人管,伊朗人如果不小心得罪了哪个美国人,呵呵。
霍梅尼上台自然是多方原因共同促成,伊朗左派当时也各种犯错,轻信了霍梅尼导致最终被清洗,但要说最大的原因,必然是英美当年为了自己的口袋推翻民主强加独裁。
民主的质量,关键在于人民对政治的参与程度与对政府的控制程度,至于什么分权制衡,什么竞争,都是无关紧要的狗屁。
今天是美国独立日。Well,又看到一大堆资本主义和保守主义纳粹哈巴狗出来刷存在感了。我只说一个史实:别看独立宣言说得漂亮,实际上,当时的人的定义,不包括穷人,不包括女人,不包括非白人,只有富裕的资产阶级是人,其他都不是人,是奴隶,呵呵。大宪章对自由人的定义也是类似的,农奴不是自由人,几百年后的人不管当时的定义与环境,一厢情愿的寻找根本不存在的狗屁“自由传统”,真是可笑啊。
经常看到有人把民主和诺贝尔奖之类挂钩,这其实是资本主义洗脑的表现,民主和诺贝尔奖之类的有个毛关系?民主只是一种人民决定政府的制度而已,非要把民主和诺贝尔奖国家强大之类挂钩,不过是恶心的资本主义成败论英雄逻辑罢了,独裁国家强大又怎样?有N个诺贝尔奖拿来又怎样?还不是当奴隶?
资本主义哈巴狗总是嚷嚷“资本主义是符合人性”的,按照这种狗屁说法,资本主义应该在20万年前智人出现时就出现了,而不是等到18世纪才开始成为世界主流。顺便,按照这种狗屁逻辑,中世纪封建制度不是更符合人性?至少持续时间比资本主义要长得多啊。
资本主义哈巴狗认为企业一定只会想着为顾客服务而不会用肮脏手段做掉竞争对手,和五毛狗鼓吹独裁政权集中力量必然会为人民办事,是一样可笑的逻辑,命题的因根本推不出命题的果。
欧洲的难民问题主要是因为和经济危机赶在一起了,经济危机时把少数群体当替罪羊是资本主义哈巴狗为了推卸责任的标准做法了,当年纳粹也是如此上台的。而在90年代出的南斯拉夫内战,实际上难民数比现在更多,但当时因为处在经济上升期,接纳这些难民就没造成多大影响(当时也有光头党,但和现在不能比)
而中东国家呢,本来社会主义还是有一些影响,在80年代之前原教旨主义都是被压制的,但后来新自由主义泛滥,政府不管人民死活,社会主义又被压制,结果导致被资本主义压迫的人民被原教旨主义骗走。
对墙内学者,自决权这点我不强求,因为共匪对这个的容忍程度比对反共言论的容忍程度都低,在墙内基本是发不出去的,但对女性和性少数群体的态度,和是否真正反压迫是直接相关的。社会主义是反对一切压迫的,没有“反对对一部分人的压迫但支持对另一部分人的压迫”这种事,这不是反压迫,而是自己想当主子
我曾经那朋友真是可笑,纳粹自称民族社会主义,他就把纳粹当左派,而DSA的全名是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美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者),然后这白痴就说DSA不懂社会主义了?呵呵,什么时候社会主义由你一个资本主义哈巴狗决定如何定义了?
顺便再说一句,资本主义如果真的是“符合人性”的,那为什么要靠谎言和暴力才能维持?
把纳粹说成社会主义,智商呢?是不是朝鲜也是民主国家啊?
珍惜?我为什么要珍惜狗屁孝道?为什么要当父母的奴隶?每次在墙内看到那些狗屁女德班,我就想吐。
对被压迫者来说,任何“合理”都是不合理,至于保守主义纳粹的嘴脸,推荐看一下Turing Point USA的言论,我曾经在推上看到他们的主席公开嚷嚷不肯承认美国价值观都得死的嘴脸。可笑这群纳粹还嚷嚷言论自由,这种屁话都说得出,还有个屁的言论自由可言?
苏联和中国以及那些模仿者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国家资本主义极权,和美国的狗屁保守主义纳粹恰恰是一路货色。共产党根本不是什么公有制,而是党官僚私有制,公有制必须建立在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基础上。
康有为也写过孔子改据考,作为一种说服策略倒没什么,但要因此认为传统文化有多先进,批不得,就太可笑了,我为什么要放着社会主义不要,而去翻那些发臭的古书呢?
民主最早当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但所谓的传统,呵呵,绝大部分是奴役压迫,后来所谓诉诸传统,不过是新观念寻找旧支撑而已,至于大宪章,这种封建运动也没什么先进的,只是后来的资产阶级故意曲解为公民权利文件而已。
柏克反民主,鼓吹素质论,这就是“成功经验”?那我还是用卢梭的人民主权论打脸好了。各国传统,呵呵,狗屁传统,基本上也就只有奴役压迫折磨虐待的“经验”了,这种经验我这个社会主义者可不会要。我的观察是,保守主义纳粹就是拿着所谓的传统所谓的权威去反民主反人权,特别是反平权,非常恶心。
有些人以为佛教是和平宗教,相比一神教,佛教的破事的确没有那么多,但别以为佛教就干净了,查查三武灭佛,查查日本一向宗,查查泰国的老虎庙丑闻,查查斯里兰卡和缅甸的佛教民族主义吧。
上世纪70年代经济停滞的时候,瑞典社会民主党曾经提出过一个雷恩—梅纳德计划,试图将大型企业经济民主化,如果这一步做成了,那么瑞典就进入社会主义了,但由于8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肆虐全球,这一步并没成功,相反90年代的时候瑞典也差点变成美国,幸亏社会民主党在发现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后终止进程。
中国右和中国左都是极右纳粹,乌有之乡和铅笔社唯一的区别在于前者拿极左外衣作为掩饰而已。
资本主义在宣传反对者时,是选择性宣传那些忠诚反对派的,例如美国民权运动,马丁路德金被大力宣传,而更激进并挑战资本主义本身的Malcolm X和黑豹党就被故意消音。
看起来有人不了解保守主义,对此我有个建议:保守主义祖师爷名叫埃德蒙柏克,google一下其言论就知道保守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了。顺便说一句,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死敌。
错,基督教本身就没有什么狗屁博爱和包容过,bible中明确写着不信上帝的都得去死,女人要服从男人,家长可以打死小孩,性少数去死,至于中世纪历史更不用多说了。
所谓的政党要由思想指导,实际上是列宁从东正教学来的控制思想的把戏,民主国家中决定政党行动的,很多时候并非思想,而是其支持者和金主,例如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就在民权运动之后对换了主张。
早期资本主义操纵供需的时候还是少数,但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互联网时代开始后,消费主义洗脑铺天盖地,想躲都躲不掉,而消费主义就是一种操纵供需的手段。
傻逼国粉纳粹经常意淫如果美国帮了他们的KMT会如何。会如何?以KMT的傻逼垃圾表现,基本就是越战的结局,最终共匪还是会统一中国;即使KMT运气实在太好,赢了,那也不会比现在的中国纳粹党更好。
傻逼极右纳粹哈巴狗们以为中国人民最惨,却不知他们亲爱的美国,非白人家庭也常年被骨肉分离。
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小政府国家,例如中美洲各国,普遍黑帮肆虐,这并不奇怪,而是新自由主义削减政府职能推卸政府责任的必然结果,政府不管,黑帮就必然填补空缺,中国农村的黑社会猖獗也是同样道理。而在中东国家,新自由主义制造的空缺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填补,从而导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崛起。
看看美国大资本在拉美的胡作非为导致当地人民如何受害,连水都用不起(因为水资源被私有化了),就知道幻想资本开放对中国人民能有什么积极作用是多么可笑。
就算用上了,对中国人民来说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墨西哥人民因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吃上了美国玉米,结果本国小农被逼得破产自杀,百万人没了生计,被迫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到美国找工作。
话说推上的巴丢草曾经做过一个调查,问中国人是否愿意接纳朝鲜难民(如果朝鲜发生战争,例如被美国攻击),结果有一半人不愿意。呵呵,这些傻逼垃圾哈巴狗极右纳粹脑残们,朝鲜人民的灾难可是你亲爱的中国人一手造成的,就这样都不愿承担责任?恶心。
如果朝鲜发生战争(无论是内战还是被美国攻击),那么必然会产生大批难民,而三八线附近是军事禁区,要穿越基本不可能,那么朝鲜人民唯一的生路就是跑到中国来,而这些傻逼纳粹们一边天天指望他们亲爱的美国大爷们发动战争,一边又拒绝接纳因此产生的难民,这是要朝鲜人民死光吗?
不少人看到现在的进步右派的主张还不错,就因此喜欢上他们主张的自由主义,实际上,自由主义本身是反对普选权,反对平权的,不少自由主义者更是支持殖民掠杀,而普选权和平权最早是谁主张的?社会主义者。
美国支持IS一样的反对派,后来又和阿萨德政权眉来眼去,一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叙利亚实际上成了多个帝国主义之间的战场,而受害者当然是叙利亚人民了
说中国这些精神老板们是“中产”,其实是不准确的,按照收入水平看,此类精神老板奴才大部分都是前5%,这已经不是中产,而是上层了。当然,他们的钱来自哪里也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屁股决定脑袋,基本都是共狗,也就不奇怪了。
极右纳粹们非常喜欢滑坡谬误,例如“允许某某就会导致其他人都开始某某”之类的,而滑坡谬误的谬误之处在于,人是有脑子的,怎么可能允许某某就导致其他所有人都去效仿呢?你看到大街上随便一个人干什么,你就会不管不顾的去模仿?可笑。
简单介绍一下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 唯物主义:一个人的行为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有先天因素,也有后天社会文化制度因素,所以不能随便说某人的行为是自己的选择,更不能把某人的行为无限制任意推广到他人身上,认为某人做了他人也会做。 唯心主义:一个人的行为完全是自己的选择,别人也会这么做。
以历史为案例思考,唯物主义的思考结果就是:某地出现文明而某地没有,是由当地的地理环境决定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和肤色种族这些毫无关联。 唯心主义的思考结果则是:某地出现文明而某地没有,是由当地人自己决定的,没有出现文明的人自己不努力,所以说明这个肤色的人都不努力,落后野蛮
有人说中国人接受丛林哲学,这有什么奇怪?你们亲爱的新自由主义的本质不就是丛林哲学吗?芝加哥哈巴狗们天天鼓吹狗屁自由市场,狗屁自由竞争,不就是丛林哲学纳粹吗?
上世纪社会主义在中东还是造成了一些影响,当时不少泛阿拉伯主义的独裁政权采用了部分社会主义政策,推行世俗化和福利制度,民间也有共产党等社会主义政党,有效遏制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但是,8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席卷世界,社会主义政党消失,福利被削减,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趁机崛起。特别要提的一个案例是伊朗,本来上世纪50年代,主张政教分离的左派民选首相莫撒啊德受到大部分伊朗人民的支持,结果就因为主张将被英美霸占的石油资源还给伊朗人民,就被美国政府秘密推翻,换了巴列维这个新自由主义哈巴狗,结果巴列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贫富悬殊,腐败严重,直接导致伊斯兰革命爆发。
社会主义者批评伊斯兰教,仇穆十字军只是憎恨穆斯林而已。
如果一个人在经济上接受了丛林哲学,那么这人怎么可能不会把丛林哲学延伸到其他领域呢?资本主义哈巴狗幻想一个人只会在经济上接受丛林哲学,而且还会遵守规则,呵呵,丛林哲学和遵守规则本身就是互相冲突的。
欧洲的殖民帝国们和美国殖民掠杀了他们的故乡,侵略毁灭了他们的国家,侵略者们当然要为自己犯下的罪行造成的后果负责了。
美国粉的本质就是纳粹粉,美国在罗斯福新政之前是个彻头彻尾的与共匪没区别的纳粹国家,后来也一直保留N多纳粹遗留垃圾,特别是红州完全就是纳粹州。美国?呵呵,事实上他们拿来吹捧美国的,都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只是他们无耻的把社会主义的成果说成美国的。
当难民可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的,若不是没有其他选择,谁会愿意当难民?傻逼极右纳粹奴才哈巴狗脑残垃圾无耻川粉们,自己怎么不滚去当下难民体会一下呢?
如果你恰巧和一个白人聊天,而他们的哲学使你确定他们的确没有种族主义,那么他们经常是社会主义者,或者他们的政治哲学是社会主义 ——Malcolm X
如果要评选全世界最无耻的奴才学者,我一定会选哈耶克,如果允许选两位,那就是米塞斯和哈耶克,如果允许选三位,那就是米塞斯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历史会记住他们的纳粹狗屁如何害得全世界穷人饿死病死冻死被打死,如何害得世界法西斯化。
何止上海,全世界的穷都是因为被压迫,而不是什么懒,要说懒,那些富人才是懒人呢,他们哪个像血汗工厂的奴工那样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还没假期了?
《通往奴役之路》,呵呵,用脑子想想,共匪为什么会允许这本破书在墙内公开出版,却不敢允许社会主义书籍出版。
最近总是看到有人说什么”民粹崛起“,其实这不过是掩人耳目,现在世界的民主倒退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长期危机引发的法西斯大潮,这在上世纪早就发生过一次了,历史又开始重复了而已,用”民粹“这种定义不清的垃圾词汇,只会模糊问题的本质。至于为什么资本主义危机会导致法西斯大潮,一句话:”外地/外国移民/外族/其他种族的人抢走了我们的工作“!这句屁话在接受资本主义洗脑的前提下是非常有效的。基本上法西斯大潮都发生在有过镇压左派历史,左派力量弱小的国家,并非偶然,而是大部分人接受了资本主义洗脑之后不知道老板们才是罪魁祸首,然后跟着老板把更弱势的人群当成替罪羊的必然结果。
1848革命就是底层革命,可笑。这种无差别杀戮事件,说到底是一种无效的阶级斗争,杀戮者不知道到底谁才是压迫他的罪魁祸首,所以错误的选择了富人的小孩作为报复对象,而那些所谓的中产呢?他们有没有管过底层的死活呢?
法西斯主义产生于欧洲?呵呵,说得好像在罗斯福新政之前的美国和共匪政权有什么差别似的,说得好像纳粹的种族隔离法律不是和美国学的似的。
当时唐纳德希特勒因为选举人制而上台的时候,我就批傻逼选举人制,但是evil这个白痴当时还反对我,呵呵;我很早就根据历史和现实认为总统制容易蜕变为个人独裁,三权分立并不是维持民主的关键因素,白痴evil也不认可,现在?唐纳德希特勒由不得他不认可了。
资本主义不在乎工人 资本主义不在乎有色人种 资本主义不在乎儿童,不在乎残疾人 资本主义不在乎性少数 资本主义不在乎女人 资本主义不在乎环境 资本主义只在乎利润
资本主义意味着最富有的1%剥削我们的劳动和统治我们。 社会主义意味着没有剥削,我们民主的自我治理。
社交媒体本身就是假新闻遍地的,不是能够当成信源的地方,真要了解此事还是google靠谱报道吧。不过社交媒体是个很好的舆论观测场所。
我曾经看到有工厂工人披露说,他们工厂里的狗屁绩效工资,有人干的多了,然后老板还不干了,觉得他拿得太多了,强行改变标准降低工资。呵呵,老板的嘴脸都是这么无耻的。
新自由主义哈巴狗否定剥削,结果就是否定了罢工的合理性,因为如果没有剥削,那么工人们也无权要求提高工资,一切由“神圣”的市场决定,呵呵。所以新自由主义逻辑必然导向反罢工以至于镇压罢工工人。所以,共匪镇压罢工,是标准的新自由主义行动。
说起共匪政府赖养老金这事,我想到了曾经玩过的一个游戏:beholder(窥探者),这个游戏是俄国人制作的反乌托邦RPG,游戏中描述了一个政府雇佣的窥探者在公寓中的经历,从头到尾都在讽刺国家资本主义极权;而这游戏后来出了个DLC叫做安乐死,内容就是:超过85岁的老人都会被政府强制安乐死。
A:老板们的理想是工人一天干二十四小时。B:错了,老板们的理想是工人一天干二十五小时。
总是看到有人一边当资本主义哈巴狗,一边又厌恶自己被强迫加班,被奋斗文化洗脑压迫,事实上,被强迫加班和奋斗文化恰恰都是资本主义的一部分,不少人羡慕的”欧美人道的资本主义“中所有人道部分,都是社会主义者强迫资本主义接受的,对,所有!
傻逼枪棍极右纳粹哈巴狗无耻脑残川粉们不知道的是,这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是思想,而不是那几条破枪。资本主义一点也不害怕那几条破枪,但是却非常害怕社会主义思想。
政府不会反恐,因为政府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恐怖组织。
没有一个人会无家可归流落街头:社会主义 穷人穷都是因为自己不努力,应该去死:资本主义
虽然乔姆斯基的表述有点不准确(真正奴役人类的是债务而不是金钱),但evil的反驳也太可笑了点,本来人类获得食物的办法有很多,但资本主义之下必须要当老板的工作奴隶才能获得食物,那么不就是被奴役吗?
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基本都是第二国际时期时社会民主党就成立并获得不少支持的国家,也就是靠近社会主义的国家。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
呵呵,资本主义哈巴狗媒体故意把社会主义者称作“极端自由主义者”?连说出社会主义这词都不敢吗?
徐水良总是批判的茅于拭,我之前并没有具体了解过,刚刚查了下其言论,这也太低级了吧?虽然其价值观是明显的奥地利孙子,但那些垃圾言论连哈耶克弗里德曼的百分之一的水平都没有,全都是那种“公共服务不够就涨价让穷人消费不起然后就够了”的傻逼逻辑,这种屁话弗里德曼要是敢说早被社会主义者骂死了。
又是这种狗屁,马克思说的公有是民主的集体所有,而私有则对应私人独裁专制拥有,你亲爱的狗屁家庭,几千年来一直都是臭男人独裁专制霸占财产压迫女人,私有制是不平等的根源是现代历史学界的共识了,傻逼滚去看看《枪炮,病菌和钢铁》中的分析吧!
多数人暴政不过是保守主义纳粹们发明的狗屁说法,看看历史和现实就知道,这世界上能维持下来的暴政都是少数人的暴政,原因很简单,多数人压迫少数人,贼赃够分吗?只有少数人压迫多数人贼赃才够分。
新自由主义既然认为剥削不存在,企业伟光正,那么唯一的结论就是反对再分配了,因为再分配侵犯了神圣的财产权,呵呵。
我很奇怪,“对生产资料和资本的私人独裁占有”这是一句很难懂的话吗?为什么资本主义哈巴狗们从来都是一副完全听不懂的表情?
每次在对资本主义哈巴狗们重复一百多年前马克思骂巴师夏和马尔萨斯们的话时,我总有一种时空穿越感。不过,谁叫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就是一百多年前肆虐欧洲,现在又肆虐了全球南方和欧美大部分国家的纯粹资本主义呢?
我不为任何国家而战;我的国家是地球;我是一个世界公民。
保守主义纳粹们的自由从来都是:我可以放火,你不能点灯;我可以屠城,你不能出声。
习特勒的目的大概是一边恢复毛教,一边继续坦克的经济模式,也就是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好处通吃。然后,再带着资本四处侵略他国,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国家。
新文化运动那时候打倒孔家店是很有必要的,但在共匪早就把孔子坟墓都掘了的今天,再把共匪的暴行说成孔教,呵呵,纯属为共匪洗地。
三权分立,呵呵,说到底,人民对政治的参与程度才是民主的关键,财团长期游说政府,腐蚀民主,最高票当选制排斥小党,还有傻逼选举人制,记得evil这个白痴咋当初我指责选举人制的时候还反对,呵呵,现在知道了吧?
真.听不懂人话。我说过无数次,社会主义反对的是资本主义的核心:对生产资料和资本的私人独裁占有,而竞争是私人独裁占有导致的一种结果,社会主义者当然也是反对资本主义鼓吹的竞争的,因为社会主义的核心是自由合作。至于资本主义贪婪之类的,这种纯道德指责,马克思当年就认为没多大意义,他的资本论的主要内容也不是指责资本主义贪婪,而是分析资本主义的极权独裁剥削压迫本质。至于乔姆斯基的演说内容,这早就是社会主义者们的共识了,《after capitalism》的作者在书中就提到了这点。
你亲爱的新自由主义主张削减福利,直接后果就是大批人饿死冻死病死,霍华德津恩早就骂过你亲爱的里根:你丫知道母亲照顾孩子也是一种非常辛苦的劳动吗?
自由市场=自由的随便企业胡作非为的市场。
他这种把一切都怪到孔教头上的逻辑,和仇穆十字军本质没什么区别。还另类右不是极右,呵呵,见过洗地的,没见过这么洗地的,还无耻的说什么基督教不是中国的主要反同力量,呵呵,推上这么多基督徒“民运”人士,装瞎啊?
中国人?全世界哪个国家的学历不是靠资源砸出来的,穷孩子哪有钱上好学校?资本主义下的教育就是一种维持阶级固化的手段,所谓的阶级上升不过是极少数个例罢了,大部分人都没那运气资源条件
反资本主义哈巴狗洗脑必备两本书:《美国人民的历史》和《海盗与君主》,前者主讲内部真相,后者主讲外交黑幕。
何止文革?毛贼就是斯大林孙子,强迫集体化人民公社,学的是集体农庄;劳改营,学的是古拉格;中央计划经济,第几个五年计划这种垃圾,也是学的斯大林的那套。对了,还有个人崇拜与造神,也是和斯大林学的。迫害同性恋者,还是和斯大林学的。
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和托洛茨基主导取消了沙俄时期压迫同性恋者的法律,并合法化堕胎,这些别说在当时,在现在,都有大批国家做不到,但对于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来说,这些早就被普遍认可了,只可惜后来斯大林把一切都毁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很多看法和做法我并不认可,但知道这段历史之后,我还是愿意对他们和其他支持他们的老布尔什维克们表示敬意的。至少在当时的环境下,没有第二个国家在平权领域作出了如此大的突破。
傻逼哈巴狗,你亲爱的资本主义公平竞争?哈哈哈哈哈,告诉我华尔街的金融寡头如何和非洲西海岸的童工们公平竞争啊?
福山是资本主义哈巴狗,他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度,其实就是资本主义下的强市场/弱民主模型,而相对的,社会主义就是弱市场/强民主模型,福山的狗屁历史终结论,吹的不是民主,而是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者早就分析过为什么资本主义下生育率低:因为资本主义把大部分人变成了无产者(很明显大部分人是生育主力,资本家再有钱也不太可能生一个班),并且无耻的把生育和抚养成本仍给家庭,实际上就是扔给了女性,又在儿童需要的教育医疗住房上面无耻的剥削掠夺,导致大部分人生不起啊。而资本家们死活都不承认这点,封杀社会主义者的言论,然后无耻的把问题的责任推到LGBT身上(中国的“民运”大部分都反LGBT平权,这也就是我为什么那么欣赏列宁在一百年前对LGBT平权作出的贡献,这一点上列宁完爆那些狗屁“民运”),恶心。
契约精神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哈巴狗拿来洗脑的狗屁概念,实际上资本主义本身从来不讲什么“契约精神”,哈巴狗鼓吹契约精神不过是要工人们乖乖当老板们的奴隶而已。说实在,就徐水良的水平,外国社会主义者随便抓出来一个都能完爆他,无非中文圈实在太烂而已。
芝加哥哈巴狗们如果还活着,我会把他们丢到中国的尘肺苯中毒等各种被老板们残害得了职业病然后被一脚踢开的受害者们面前,然后要他们跪下来为他们的狗屁自由市场造成的罪恶谢罪!
这些资本主义极右傻逼纳粹哈巴狗脑残奴才川粉既然这么喜欢工作,那就把他们丢到古拉格里天天工作个够吧,呵呵。
新自由主义鼓吹的狗屁企业家精神有两点:创新和承担风险。创新,呵呵,世界上大部分独裁企业狗屁创新能力都没有,绝大部分创新都是员工做的,然后被老板们无耻的盗窃霸占;而承担风险,呵呵,老板们利润率一下降,首先就是降薪裁员,无耻的把风险转嫁为员工,员工没了工作就得喝西北风去,这不是风险?
这类垃圾基本来自美国,因为西欧和北欧社会主义力量强大,这种垃圾在那边没什么市场,而美国,呵呵,成型的左派力量迄今都没有,两党一个右一个极右,结果资本主义哈巴狗四处蹦达,最终蹦达出了一个唐纳德希特勒出来。
无耻的新自由主义垃圾把财富来源说成狗屁“企业家精神”,无耻程度堪比基督教鼓吹上帝造人,共同点:屁证据支撑都没有。
资本主义:我创造了财富。 社会主义:劳工创造了财富,而你不过是无耻的劫掠了财富而已。
哈哈哈,这不是新自由主义哈巴狗们的典型狗屁吗?政府我还能通过选票控制,富人我完全控制不了一点不透明,至于经济发展?呵呵,是拿钱买奢侈品炒高房价促进了经济发展,还是拿去游说政府破坏民主或者转移到避税天堂促进了经济发展?
奴隶制虽然没人发工资,但奴隶主必须负责食宿,现在的很多工作奴隶连食宿都负担不起,还不如古代奴隶制呢。
一直都无法理解那些认为经济发展就能自动带来民主的奴才的逻辑:独裁者吃肥了就会良心发现了?这什么狗屁逻辑?
任何形式的压迫都必须依靠压迫性的制度才能维持,所以任何压迫都与民主本质上冲突,换句话说,无论你想要压迫谁,都别想得到民主,这种社会的民主形式也绝不会稳定存在,要么消除压迫,要么蜕变回独裁。
“如果要推翻现实中的国王,必须首先推翻大脑中的王座!”这句话中的“推翻大脑中的王座”有两层含义:1,不能在王座上摆放任何东西,人或上帝都不行;2,自己也不能坐到王座上,不能在别人之上。简单来说,就是必须要砸烂王座,无论谁,包括自己,都不能坐。跪着的奴才得不到民主,想要别人下跪一样得不到.
根源在于资本主义下的强市场/弱民主制度本身就不稳定,民主被财团游说所侵蚀,特别是这几十年新自由主义肆虐导致民主越来越被腐蚀,社会主义被打压,造成真空使得极右崛起。
傻逼中国无耻脑残垃圾奴才纳粹臭男人们,你们嚷嚷找不到老婆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先想想被你们亲爱的家长们屠杀的女婴啊?
历史发明家徐水良真应该滚去看看罗伯特道尔的《论民主》,1831年只有3.1%的英国人有投票权,这算个屁的民主国家?同时期美国基本也是这个比例,狗屁民主国家,资产阶级的oligarchy而已,有什么可吹的?
民主是由农民推动的?真是历史发明家啊,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实际上根本就没带来民主,而是资产阶级击败了封建地主之后搞的寡头商人小圈子独裁,此时大部分人根本没普选权;后来直到19世纪,英国的工人和农民们才开始进行宪章运动,女性获得投票权更是要到一战之后了,这其中最大的推动力是社会主义。无论你徐水良如何污蔑马克思,马克思都是明确支持工人们争取选举权的,并亲自参与工人运动,即使是列宁,其帝国主义理论与民族自决权,还有取消沙俄时代迫害LGBT的法律,都是很有进步意义的,你这傻逼还是别装瞎为好,呵呵。
那些嚷嚷为了人类的傻逼极右纳粹奴才哈巴狗脑残狗屎,如果让他们自己去为了人类牺牲一下,他们马上不干,呵呵。
恩格斯说的是真相,资本主义会将一切都变成商品,包括人。
你亲爱的美国本来就没什么福利,新自由主义肆虐之后更是流浪汉满大街,穷人连房都租不起天天被驱逐,狗屁吃福利,呸。
资本主义意味着资本的所有者剥削和统治我们当中的其他人。 社会主义意味着没有剥削,工人们民主的治理自己。
是的,资本主义是伟光正的,我曾经那个朋友就是如此,还无耻的说资本主义创造财富,哈哈哈哈,创造财富的是劳工,他亲爱的资本主义不过是无耻的剥削掠夺了劳工们的剩余价值而已。
他还吹捧美军是自由之师,然后我把越战历史拍他脸上,然后,他很无耻的说,屠杀是韩军干的,美军参与者后来主动忏悔了。呵呵,事实是,每支美军部队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美莱大屠杀,而当时美莱大屠杀一开始被军方掩盖,结果后来实在掩盖不住了才承认的。
如果所谓的文明就是要让我们卑躬屈膝,那么我们就让你们看看野蛮的骄傲!我曾经那个朋友竟然认为暴力强迫一群人接受他所谓的“先进文明”没问题,呵呵,然后他还好意思说我专制霸道。
话说我曾经那个朋友鼓吹军国日本殖民台湾和东北带来文明,我拿了一大堆历史资料去打他的脸,结果他非常无耻的说:殖民和杀戮不是一回事,呵呵,如果殖民都能被如此定义,那么我也可以重新定义一下中共。
C:资本主义下越优秀的公司就越有竞争力。 S:优秀?你说的优秀是指压榨劳工坑骗消费者游说勾结政府污染环境垄断知识的能力吗?资本主义下的狗屁竞争必然是逆淘汰的,越会抢掠的越容易胜出,而有良知的老板根本别想做大。
她对斯宾塞主义有洗地嫌疑,斯宾塞当年鼓吹斯宾塞主义,本意就是为当时的纯粹资本主义洗地,因为当时已经爆发了1848革命,虽然在大部分国家都失败了,但压迫者们也感受到了威胁,而社会主义者更是完全否定竞争,或者说,资本主义鼓吹的竞争本身就是逆淘汰的,这是资本主义的结构决定的,外部制约没用。
没错,共匪其实就是和共和党的”law and order”(法律和秩序)学的,然后我曾经在推上讽刺,拿法治说事的反贼不是吃法律饭的就是傻逼奴才。国际歌第三段:压迫的敌人,空洞的法律,富人不承担任何义务,穷人的权利是一句空谈!
哈哈哈哈哈,奥巴马只是个符号而已,可没法说明消除歧视。穷黑人的待遇才能真正说明歧视问题。
纳税人这种狗屁概念,呵呵,现代政府的责任是捍卫所有人的基本人权,无论是否纳税,更何况现代社会没人不纳税,即使是“非法”移民,只要进来正常生活了,也必然纳税。 至于这种傻逼种族主义,呵呵,当年马克思就骂过这些垃圾,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
福山这条资本主义哈巴狗鼓吹的狗屁历史终结是典型的历史决定论,结果没人反对,呵呵。
美国帝国主义无耻的侵略拉美,毁了拉美人民的家园,把他们逼迫成难民,现在还要害得他们骨肉分离!
这有什么奇怪啊?新自由主义哈巴狗们嚷嚷狗屁私有化,然后共匪把医疗私有化了,进入自由市场了,结果如何啊?把基本人权当生意,和贩奴有什么区别?
资本主义建立在盗窃之上。 工人们生产了所有组成社会财富的产品和服务; 统治阶级们什么也不生产,却霸占了大量财富; 保卫资本主义就是保卫大规模的,纯粹的和简单的盗窃。
傻逼资本主义哈巴狗经常拿“没工作”(实际上是没当老板的奴隶)去攻击别人,呵呵,没你们亲爱的工作又怎的?大赦国际人权观察这类人权组织可是靠捐款活着的,没给你们亲爱的老板们当奴隶,但他们能把你们完爆了,知道吗?你亲爱的资本主义故意制造失业大军,还来攻击受害者了?无耻。
我曾经那个朋友对我对军国日本的态度很不满,然后说共匪也反日,然后我回复说:你知道不知道共匪和军国日本政府是相互勾结的?你知道不知道共匪把日本战犯都放回日本去了?你知道不知道80年代中日蜜月期的时候,共匪根本不准当年的受害者说出真实的历史?
美国的革命社会主义者被军队开除了,然后那些嚷嚷言论自由的狗屁保守主义纳粹哈巴狗们屁都不敢放一个,呵呵。
傻逼纳粹极右脑残哈巴狗奴才川粉们在吹捧他们的白大爷的时候,从来都没吹捧过东欧和俄国人,更没吹捧过伊朗人,阿拉伯人,柏柏尔人,突厥人,可人家也是白大爷啊。
你亲爱的奥地利芝加哥奴才哈巴狗们始终无法面对马克思指出的生产资料和资本被私人独裁占有这一关键问题,扯淡财富来自主观感受,老板们的财富来自狗屁企业家精神,这和基督教说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又有什么区别?
你亲爱的资本主义哈巴狗是反对普选权的,社会主义者铸造了欧洲的民主,铸造了现代文明,不爽可以滚回19世纪体验纯粹资本主义。
最早主张普适的个人自由的是社会主义,只是后来新自由主义哈巴狗们故意将自由偷换为“经济自由”(其实就是老板们胡作非为剥削掠夺投机赌博的自由),制造了虚假的“平等与自由的对立”。
资本主义哈巴狗们喜欢吹捧的那些古典自由主义者,其实基本都不支持普选权,最早主张并推动争取普选权的, 是社会主义。
傻逼胡平,这种研究就是狗屁,智商这种垃圾狗屁概念连个公认定义都没有,很多所谓的智商测试不过是测的做题套路,屁都说明不了,还拿来说事了?傻逼。
话说tor的开发者是傻逼纳粹极右脑残奴才垃圾哈巴狗川粉们最讨厌的“白左”,实际上自由软件的开发者基本都是“白左”,呵呵。所以傻逼川粉们千万不要用自由软件哦!
对于所谓的“贵族精神”的崇拜也是奴性的一种表现,幻想贵族救世主们会主动来拯救自己,呵呵。
资本主义之前的制度不仅不鼓励“阶层上升”,而且谁敢鼓吹基本就是个被杀头的下场,例如谁来一句“穷人可以做皇帝”“贱民可以当贵族”,呵呵,直到资本主义从18世纪开始成为世界主流,狗屁奋斗文化才开始流行,“从乞丐到老板”,呵呵,实际上不过是骗人的狗屁罢了。
有傻逼垃圾白痴新自由主义纳粹无耻奴才哈巴狗经常拿奥威尔的《1984》攻击社会主义,呵呵,我说傻逼在攻击之前也不知道查查,奥威尔可是个社会主义者,还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帮助过西班牙共和派来着,不信的滚去看看《向加泰隆尼亚致敬》吧。奥威尔看到西班牙共和派在斯大林的影响下变得越来越残暴,主动屠杀社会主义者们,由此写出《1984》,所以这书根本就是讽刺斯大林极权的,包括后来的《动物农庄》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文库还把这两本书放在左翼文化栏里面呢。
就推上很多“维权人士”真没资格叫唤自己有多惨,在墨西哥,人权捍卫者可是一直不停的被直接谋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