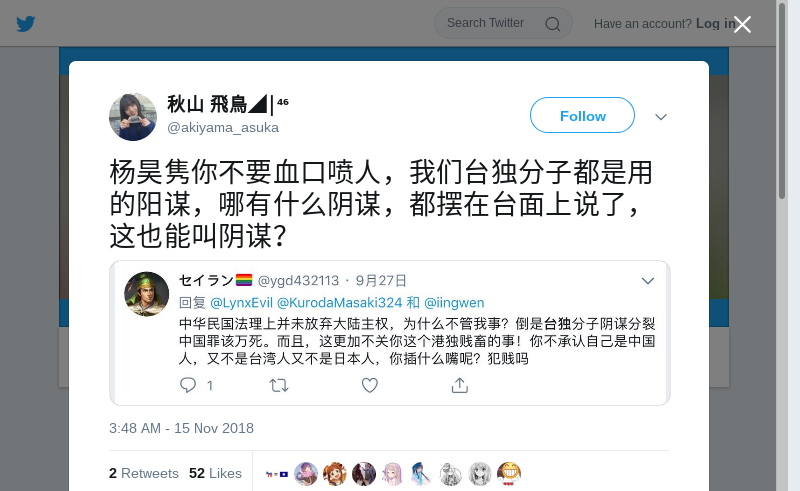兒童是被壓迫的階級,在父權制家庭制度的統治下受苦。同性戀解放組織意識到兒童在傳統家庭之下失去自主權,並受到各類壓迫,並開始引導解放兒童的社會運動。
作者:Michael Bronski
翻譯:七音
編輯:xd Targaryen
美編:太子豹
1972年,於三年前(1969年)的石牆騷亂後成立的最具影響力的同性戀解放組織之一——波士頓男同性戀解放組織(Boston’s Gay Men’s Liberation)的成員驅車前往邁阿密,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遞交了一份含有十項訴求的宣言(文末附有全文翻譯)。在新的酷兒政治意識、女權主義和義憤的交匯下,這份宣言應運而生,表達了一種烏托邦式的政治願景。它涵蓋的內容十分廣泛,其涉及的領域遠遠超出我們現在對LGBT政治的定義。例如,它的第一個要求就是「停止任何基於生理上的歧視。任何政府機構都不應記錄膚色、年齡和性別。生理特徵永遠不應在法律上造成任何歧視或特權。」
 1970年的「同性戀解放日」,華盛頓「馬太辛協會」成員在紐約街頭。
1970年的「同性戀解放日」,華盛頓「馬太辛協會」成員在紐約街頭。
圖片來源:
四十五年過去,如果說男同性戀解放組織的許多要求仍有爭議,但大部分要求在今天的政治語境中卻仍然清晰可辨:該組織試圖結束美帝國主義,防止基於性別認同的歧視,並廢除警察制度。許多激進左翼人士在今天依然有上述訴求。然而,該宣言中的第六項要求,即使是對於今天的許多活動家來說,都顯得不負責任、異想天開並有些危險,可能引發社會動盪:
撫養孩子應該是整個社會共同的責任。應該解除父母對「他們的」子女的任何合法權利,每個孩子都應該自由選擇人生。要建立免費的全日託兒中心,讓男女同性戀者共同分擔撫養孩子的責任。
集體育兒?在法律上解放兒童?酷兒們幫助撫養其他人的孩子,並且作為榜樣和道德楷模?當保守派們警惕共產主義赤旗下自由的「社會改造」(social engineering)時,他們所害怕的不正是這種蘇聯的教育日托所在美國的酷兒版本嗎?
還是說,它是一個將女性最終從生育負擔中解放出來的烏托邦,同時創造了一種社會結構,在這個社會結構中,孩子們可以作為獨立個體放心地活動,不會因為探索「性」而感到恐懼或羞愧?
「童年」是成年男性為了壓迫女性創造出的概念
至少從十八世紀以來,關於童年的本質一直存在激烈的爭論。孩子們是否天性本善,是適合開放的勞動力市場,還是需要標準化教育?這些問題在幾個世紀以來引起了兩極分化的觀點,但大多數改革者已經在不同程度上都認為,兒童需要成年人的保護,作為交換,他們享有較少的基本權利。
無論先前的許多改革有多麼進步,20世紀60年代後期的兒童解放運動都是巨大的突破,因為它否定了兒童應該由家長撫養。在成年人(從嬉皮士、激進女權主義者到民權主義者或早期同性戀平權者)尋求更大的個人自由的文化背景下,年輕人認為自己是(或被認定為)被壓迫的少數,從而尋求享有法律上的平等和解放,也許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20世紀60年代的激進主義本質讓我們知道,兒童解放並不是一個題外話,而是爭議的核心。保羅·古德曼1960年最暢銷的書《荒謬地成長:組織系統中的青年問題》(Growing Up Absurd: Problems of Youth in the Organized System )提出,兒童是資本主義橫衝直撞下的首批受害者;而同年A·S·尼爾的具有前瞻性的教育論文《夏山學校:一種激進的育兒方法》(Summerhill: A Radical Approach to Child Rearing)提出,兒童可以作為民主行動者,做出明智的社會選擇和性選擇,而且他的學校多年來一直在此方向教育他們,這種教育方法沒有任何不良影響。
當中古史學家菲利普·阿希葉的《童年世紀:家庭生活的社會史》在1962年以英文出版時,也一樣引起了轟動,這本書追溯了西方國家「童年」的詳細歷史,證明我們現代的「童年」概念——即孩子必須被保護在世界之外——只是近年的社會建構。核心家庭也是如此。 阿希葉表示,在歷史上大部分年代,除了最年幼的孩子以外,其他兒童都像成年人一樣生活於世。
《夏山學校》一書在1960年至1970年銷售量超200萬,而古德曼的 《荒謬地成長》在出版的最初幾年銷量也超過了10萬。兒童解放的政治語言很快取代了理論和猜想。在20世紀70年代,至少有15本面向大眾的書籍宣傳兒童權利和兒童解放思想,包括大衛·古利布的《兒童解放》(1973)、比阿特麗斯和羅納德·格羅斯的《兒童權利運動:戰勝青年的壓迫》(1977)。
而當這些想法與新出現的女性解放話語相結合,就發生了更為激進的轉變。例如,舒拉米斯·費爾斯通在其突破性的《性別辯證法》(1970)一書中指出,生理生殖本身是女性壓迫的核心,並呼籲採用新技術來取代分娩。此外,她還認為,兒童是被壓迫的階級,在父權制家庭制度的統治下受苦。費爾斯通在「打倒童年」一章中爭辯說,「童年」這一階段的產生以及「童年無辜」(childhood innocence)的概念是成年男性為了加強對婦女的壓迫而創造的建構,而這也是核心家庭的功能。凱特·米利特在1984年的論文《超越政治:兒童和性》中進一步指出,兒童的壓迫明顯源於否認他們的性認知:「性本身對兒童是一種罪惡。這就是成年人如何控制孩子並禁止他們的性行為的。這種觀念已流傳許多年了,而且對成年人來說無比重要。」
同性戀解放兒童
同性戀解放組織受到婦女解放組織的啟發,許多人希望在他們的行動中加入童年和教育學的話題。然而,僅僅因為表達了對兒童的理論興趣,他們就面臨著被當做是戀童癖的風險; 畢竟,當時大多數美國中產還是認為男同性戀是變態者。 一些同性戀作家採取了立場,直接承認大多數同性戀者都知道而大多數異性戀者卻試圖拚命否認的事實:同性戀兒童是存在的。面對著種種謬見——即成年女性和男性「選擇」去當同性戀或者被墮落的成年人誘惑成為了同性戀——同性戀解放者講述了他們自己作為同性戀兒童的故事,並根據正如凱特·米利特的理論認為,對青少年來說,性壓抑和缺乏性知識遠比同性性行為更危險。 卡爾·威特曼,在石牆騷亂前一個月發表的具有奠基意義的《同性戀宣言》中寫道:
關於剝削兒童的說明:孩子們可以照顧好自己,並且比我們願意承認的時間更早就意識到了性。我們這些在青春期早期就開始在公共場合獵艷的人都知道這一點,我們這是在尋歡,而不是被老色鬼勾引……至於對兒童猥褻的行為,絕大多數都是異性戀男人對小女孩做的:這不是同性戀特有的問題,而是由反對肉體之歡的禁欲主義所帶來的挫敗引起的。
 石牆騷亂。圖片來源: Leonard Frank
石牆騷亂。圖片來源: Leonard Frank
僅僅談及同性戀兒童的存在就衝擊了恐同人群的核心。成年同性戀說他們還是孩子時就已有了特別的性慾,這類證詞是公眾關於同性戀話題的新發展,也是一個大膽的政治策略。事實上,在一個新興的兒童解放運動的背景下,證明同性戀青少年和兒童的存在對政治組織產生了直接影響。石牆騷亂後不久,隨著同性戀解放組織遍布全國各地,青春期的酷兒們也開始組織起來。在《紐約的同性戀解放青年運動:「戀人永不言敗」》(The Gay Liberation Youth Movement in New York: ‘An Army of Lovers Cannot Fail’,2008)中,史蒂芬·L·科恩記錄了十年間至少三十個美國LGBT青年成立並運作的組織。
更激進的理論家認為,一旦人們接受了資產階級家庭壓制兒童性行為的觀點,按邏輯來說下一步就是要求結束核心家庭,並讓男女同性戀者參與兒童養育。儘管其意識形態的純潔性可能使其有些極端,但在當時,政治運動範圍延伸到育兒領域並不是越俎代庖。其他政治運動已經在處理如何去定義兒童及其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之類的問題。例如,黑豹黨建立了他們自己的學校和課外項目,還有免費早餐的計劃,將自身參與到既有的公立學校系統。
主流和激進的女權主義者成立了女權主義日托中心。他們還出版了沒有性別歧視的兒童書籍。最著名的包括馬洛·托馬斯1972年的插圖書和唱片《自由地去做……你和我》(Free to Be . . . You and Me),鼓勵性別平等;還有夏洛特·佐洛托1972年的創作的圖畫書《威廉的娃娃》,書中一個男孩想要一個玩偶當禮物,讓他注重性別規範的父親大為惱火,因為娃娃一般被認為是女孩的玩具。
同性戀家庭的誕生
堅持認為男女同性戀能夠幫助撫養孩子,這是改造傳統家庭的一種激進觀點,但其目的不僅在於塑造兒童,也在於塑造成年人:許多活動家認為,只有當他們能夠參與撫養社會下一代時,他們的公民權利才能充分地被享有。
但我們也要客觀地去看到,多年來,成年酷兒們一直在撫養被家人發現性取向並離家出走的酷兒兒童,特別是在紐約西村和舊金山卡斯楚等同性戀聚居區。無家可歸的酷兒兒童,無論是自己選擇還是被環境所迫,都往往會湧向這些街區,在那裡他們常常被好心的成人收養。例如,Sylvia Rivera和Marsha P. Johnson於1970年創辦了街道異裝運動革命陣線(Street Transvestite Action Revolutionaries,STAR),在曼哈頓為無家可歸的跨性別青年設立收容所。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同性戀俚語中,如果一個年長的男同性戀者接受了給新來的年輕男同性戀者提出指導或建議的任務,他就會被稱為「媽媽」(mother)。
 由跨性別組成的酷兒家庭 圖片來源:《姿態》劇照
由跨性別組成的酷兒家庭 圖片來源:《姿態》劇照
這符合20世紀70年代早期流行的「同性戀家庭」概念:不具有傳統家庭關係的、一種延伸了的,通常是跨代的朋友們互相支持,就像一個生理家庭那樣。在社區中建立家庭,對於當時許多LGBT人群的日常生活至關重要,說實話這是在挽救生命。這種家庭的活力在70年代末十分明顯,當時Sister Sledge的熱門歌曲「我們是一家人」(We Are Family)立即成為同性戀酒吧的最愛,並且經常被作為LGBT社區舞會和同志驕傲遊行的最後曲目播放。在愛滋病流行期間,對同性戀家庭的需要更為迫切,因為許多原生家庭拋棄了他們生病的兒子,而傳統的療養社區也崩潰了。
換句話說,同性戀者多年來一直在創造和養育家庭,這些家庭比起核心家庭提供了諸多優勢——特別在身體和情感安全上。然而,他們不希望這種家庭再被視為是二流家庭,他們想要讓所有人從父權制和資產階級價值觀的殘暴枷鎖中解放出來。
酷兒育兒的實踐
然而,男同性戀解放組織的要求從來沒有實現,對於如何進行實際操作,「十點要求」的作者往往只有雛形。同樣,紐約同性戀解放陣線的一些男性成員也離開了該組織,他們認為這個組織不夠女權主義,並建立了男同性戀革命女權組織(Revolutionary Effeminists)。歷史學家馬丁·杜伯曼(Martin Duberman)在2018年的對LGBT運動的分析《同性戀運動失敗了嗎?》寫道,男同性戀女權主義者「認為男同性戀者也應該為女性服務,承擔傳統的家務,包括撫養子女,以此促進女性力量的崛起。然而,似乎男同性戀女性主義者也沒能將理論付諸實踐,而且這個團體的成員從未擴大,因此很快就消失了。
儘管如此,在地方層面上,酷兒育兒的實踐以不太激進的方式發生。除了上面提到的同性戀實際收養的例子,1975年波士頓的一些同性戀和異性戀男性——他們與男同性戀解放組織並無聯繫,但可能受到其要求的啟發——形成了男子育兒組織(Men’s Child Care Collective)。雖然該組織有意識地被塑造成一個異性戀/同性戀聯盟,但關於該組織的公布的極少量的報導總是將其稱為「男同性戀的育兒組織」。這個口誤可能說明了這一事實:該組織中絕大多數是男同性戀。
該組織在波士頓市中心布羅姆費爾德街22號的布羅姆菲爾德街教育基金會會面,在那裡《男同性戀社區新聞》和《Fag Rag》(男同性戀解放組織的分支)的出版物都有自己的辦公室。大多數會議都是為了提高意識,討論男同性戀如何和異性戀男性成為朋友,如何共同合作。並且,作為一個進步的,制定女權主義思想的男性組織,他們也討論要通過分擔照顧孩子的工作以幫助女性。
他們開展的一個具體項目是為在劍橋參加酗酒互助協會的婦女設立一個日托小組。他們還在LGBT和進步政治會議上志願提供日托服務。該組織的一個重點是向以各種方式被邊緣化或處境艱難的婦女提供兒童保育。他們的女權主義理論既反映了男同性戀解放組織的一些要求,也有對階級、經濟和種族問題的關注。像許多政治團體一樣,男子兒童保育會持續了幾年。後來成員離開波士頓或更多地參與其他項目,該團體便解散了。
包括舊金山、聖克魯斯和紐約在內,全國各城市都有了類似組織。這些組織的目標有三個。作為女權主義者,成員們承諾減輕一些女性照顧孩子的負擔。他們也會有意識地反對一些限制性的性別角色,即男性不應照顧和養育兒童。也許最重要的是,他們決心通過言語和行為來對抗一個根深蒂固的迷思——同性戀是猥褻兒童者。
核心家庭的復歸
然而,儘管包括波士頓男子育兒會在內的這些團體在觀念上都是激進的,他們也奇怪地有傳統的一面,因為他們傾向於把男同性戀者置於異性戀關係中,讓他們作為孩子的臨時看護人。而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看護孩子的女同性戀中的大多數也是已經離異了的。在某種意義上,女同性戀們或男同性戀們一起養育「自己的」孩子這一想法,至少再過十年才會開始萌芽。而當它出現的時候,它通常仿照而非挑戰異性戀的核心家庭模式。隨之而來的是,在同性戀平權活動中,近乎崇拜地將同性婚姻優先於所有其他目標之上。激進的同性戀解放組織的目標是顛覆核心家庭,但取而代之的是這項同性戀權利議程,它通過重新在核心家庭中注入象徵意義和現實必要性,賦予核心家庭新的生命。
到1977年,美國全國保守主義運動的興起,讓隆納·雷根入主白宮。它還預示著高度組織化的「道德多數派」運動(他們在道德及宗教上觀念強硬而保守)的出現,將右翼福音派新教的話語注入政治。 在這一背景下,反同歌手安妮塔·布萊恩特(Anita Bryant)在攻擊一項LGBT反歧視法案時,提供的原因是「把我們的孩子從同性戀中解救出來」。布萊恩特領導了全國性的「救救我們的孩子」(Save Our Children)運動,採用了美國現代歷史上長期以來使同性戀者深受其害的騷擾、虐待和洗腦手段。
同性戀平權運動不再以事實,或最起碼以同性戀年輕人的證詞來與這些謊言對抗,而是放棄了與兒童和青少年的一切關係。同性戀社區中心對贊助同性戀青年團體猶豫不決。 社會對於男女同性戀合法收養兒童的討論漠不關心。所有關於將LGBT材料引入課堂的討論都被擱置。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里,政治討論從集體照顧兒童,同性戀家庭轉移到私有化核心家庭的婚姻平權。在更大的政治背景下,關於兒童解放的討論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保護兒童免受性侵害,免受「不良」音頻的浸染,免受潛伏的捕食者猥褻。
 美國最高法院外,反對《捍衛婚姻法案》的示威者。
美國最高法院外,反對《捍衛婚姻法案》的示威者。
近幾十年來,爭取婚姻平等的鬥爭對於同性戀平權運動的成功至關重要。然而,對於我們這些回憶起從前富有政治遠見和活力以及激進變革潛力那段日子的人來說,這一勝利喜憂參半。用同性核心家庭代替傳統的異性戀家庭,並不一定能根除這種體制帶來的危害甚大的結構性問題。同性戀解放組織關於兒童的策略和理論方法是個複雜的政治問題。它們有的實際,有的則異想天開,但動機都是渴望能認真照顧兒童,以及希望徹底打破充滿壓迫的家庭結構。憑心而論,這些各種各樣的運動——從證明同性戀兒童的存在,到照顧兒童,再到破壞允許父母「擁有」孩子的法律框架——不僅是同性戀解放組織為重塑世界做出的嘗試,也是為了治癒數十年來社會(尤其是同性戀者的原生家庭)對同性戀們造成的傷害。
半個多世紀以來,這種療愈在許多方面潤物無聲。數量驚人的青年紛紛越來越早地公開同性戀身份。而關於酷兒青年性行為和性別角色的討論也日益複雜,充滿活力。如同1972年的同性戀解放運動開始想像的那樣,孩子們現在都沒事,他們自己把自己照顧得很好。
原文連結:
附:
波士頓男同性戀解放組織的「十點宣言」:
 波士頓同性戀解放陣線敦促將以下原則納入1972年民主黨綱領:
波士頓同性戀解放陣線敦促將以下原則納入1972年民主黨綱領:
1. 我們要求結束一切生理歧視。任何政府機構都不應記錄膚色,年齡和性別。生理特徵永遠不應成為任何特殊法律歧視或特權的基礎。
2. 我們要求停止一切基於性取向的歧視。每個人都應該自由地獲得性滿足而不必擔心被強姦。政府既不應使這些滿足形式合法化,也不應使之非法化。任何人都不應該因為自己是同性戀而在行動(無論是移民入境還是出境)、就業、住房或其他方面受到限制。
3. 美國政府不僅應該結束對穿衣習慣的歧視,還應該積極鼓勵更具想像力的著裝。 任何武裝部隊或其他政府機構的成員都不應該被強迫穿「制服」,以符合生物性別或等級地位。 例如,如果他/她們喜歡,女性應該被允許留短髮和穿長褲; 而男性可以留長髮和穿連衣裙。
4. 應該停止對男女同性戀者的一切經濟歧視。我們不應該因為性取向或著裝習慣被剝奪就業或晉升的機會。我們應該與生活在核心家庭中的異性戀者享有同樣的稅收優惠。我們也應該和所有人一樣有充足的食物、住房、醫療服務和交通工具,以便過上充實有益的生活。我們特別支持為每個人提供5,500美元的基本收入,我們呼籲重新分配國家財富。資源和權力必須從白人異性戀男子那裡奪走,重新分配給所有人。
5. 我們呼籲停止所有關於「同性戀」的政府(或其他)研究。我們的性取向不是疾病; 所有化學、電擊或催眠「治療法」來「治癒」同性戀都應該是非法的。現在用於「精神健康」的政府資金應該給男女同性戀者和其他「精神病患者」群體,以便他們可以在諮詢和社區中心組織起來以滿足自己的需要。
6. 撫養孩子應該是整個社區的共同責任。父母對「他們的」孩子的任何合法權利都應該被解除,每個孩子都應該自由選擇自己的命運。應建立免費的二十四小時託兒中心,讓男女同性戀者在那裡分擔撫養兒童的責任。
7. 現在所有因任何「性犯罪」(強姦除外)而被監禁的男女同性戀者應立即從監禁室、精神病院或監獄中釋放。他/她們應得到每監禁小時2.50美元的賠償;所有監禁記錄都應被銷毀。因其他指控而被監禁的男女同性戀者應免於被獄卒或囚犯毆打和強姦;任何人都不應因在禁閉期間從事「同性戀行為」而被剝奪迅速釋放或假釋的權利。
8. 我們呼籲停止所有有目的的侵略力量。我們支持越南人民的七點和平計劃,並呼籲所有美國及其支持空軍、陸戰隊和海軍部隊從越南完全撤離。此外,我們呼籲所有美國軍隊返回美國境內,作為結束美帝國主義的最有效方式。
9. 在美國,我們要求解散所有武裝部隊、秘密警察(聯邦調查局、中央情報局、國稅局、禁毒隊等)和制服警察。武器應該只用於保護人民和防止強姦。為此目的,我們呼籲建立一個人民警察機構,由現在最容易遭受警察暴行的人組成:第三世界團體、婦女、男女同性戀者和窮人。
10. 我們要求,不論國家、性別、黨派、種族、年齡或其他人為強加的類別,所有人民都有自治和自決權。只要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成為他人的財產或奴隸,我們的解放運動就仍未完成。所有強權和統治必須結束,必須建立平等制度。我們必須共同尋求新的合作形式。
原文網址:https://read01.com/oLPEze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