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逐(eviction),是指房东对租户的强制驱赶行为。它集中发生在极端贫困的人群中。对于他们来说,即使是最廉价的房租,也会花费月收入的一半到百分之七十以上。驱逐,这种在几十年前会引发群众公开抗议的现象,在21世纪的美国已经变得制度化、产业化和日常化了,其形式通常也十分简单粗暴:房东对租户下驱逐令以后,搬家公司的雇员和地方行政官随即执行,把租户的所有物品强行搬清。现在,全美一年被驱逐的租户就有几百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Matthew Desmond根据他的博士论文修改发表的《遭遇驱逐:美国城市的贫与富》(Evicted: 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一书对这一现象做了深刻的分析。该书在受到美国各大主流媒体好评以后,因为斩获了今年的普利策非虚构类奖项,而受到了更加广泛的关注。这本书因为其充实的素材和饱满的写作风格而向非学术圈的读者敞开了怀抱。这部作品是他早期关于自己家乡亚利桑那州的山火消防员的民族志《在火线—与野外消防员同生共死》(On the Fireline—Living and Dying with Wildland Firefighters)之后的又一力作,以此奠定了他城市社会学和贫困问题研究者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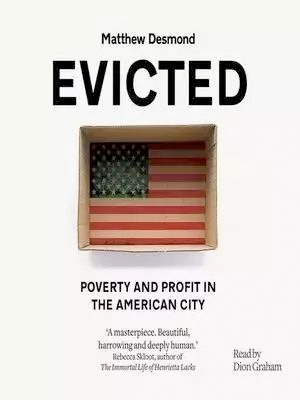
在Desmond研究的城市——人口不足60万的Milwaukee,每年就有一万六千多人被驱逐。这还只是通过驱逐令这种正式手段被驱逐的人数,如果算上各种非正式的驱逐手段,那么从2009到2011年之间,全市超过八分之一的租户至少经历过一次强制搬迁。因为被驱逐的历史与个人信用记录和社会保障号挂钩,很容易被房东查看到。因此,有被驱逐经历的租户,本来住房选择就很稀少,在一次次地被驱逐中,他们的选择便不断降低,最后减少到几乎为零。于是,被驱逐的男女老少在条件极其危险恶劣的住房和收容所之间辗转挣扎,要么就流落街头。
驱逐,这瞬间威胁到人最根本生存的恶性循环,在美国全年不停上演:不管是过生日,圣诞节还是历史上最冷的冬天,Desmond书中的租户都被驱逐过。而这些租户是从怎样的居住条件中被驱逐出来的呢?在2009到2011年之间,全Milwaukee有一半的租户面临着长期而严重的住房条件问题:没有供暖、窗户破损、下水道拥堵、蟑螂老鼠泛滥。
在Desmond的眼中,驱逐这一普遍而又残酷的现象,反射了美国贫困问题和社会不平等的各个层面。于是,他通过亲自在Milwaukee的两个不同的贫民区——贫困黑人聚集的北区(North Side),和贫困白人聚集的活动房公园(Trailer Park)——租住的观察和经历,向读者们展示了生活在这两个不同的地区的八个家庭的命运。他深入城市里,去感受最走投无路的人们的日常生活,以社会学的视角观察和揭示了驱逐——这一足够对城市贫困人群造成长期和毁灭性打击的现象——所涉及的方方面面。

阶级、种族、性别与住房:历史与结构的罗网
从二十世纪下半叶开始,曾经在二战以后一度十分蓬勃的美国各大传统工业城市陆续开始了去工业化的进程。资本对廉价劳动力的寻求,使制造业等行业向海外和南方缺乏工会力量的州迁移。这造成了位于美国中部的威斯康辛州的Milwaukee的衰败:仅在1979到1983这四年之间,这个城市丧失的制造业岗位比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还要多,而这一经济困局对黑人工人阶级的影响最为严重,因为他们中有半数集中在制造业。从80年代到90年代,黑人贫困率从28%飙升到42%。2008年经济危机更使该城市受到重创,而Desmond的田野工作就是在这一时间段进行的。
60年代,Milwaukee曾经被纽约时报称为“美国隔离最严重的城市”。即使经历了民权运动的洗礼、本地居民的抗议和美国国会来之不易的居住平等法案以后,Milwaukee中的种族歧视和居住隔离,迄今却仍旧基本保持着当年的格局:无业和底层工人阶级黑人仍旧集中居住在北区,贫困白人因为墨西哥裔的人口增长向更南的方向搬迁,居住在一河之隔的南区。而Desmond第二个田野地点——活动房公园——就在这个地区。在这两处进行对比,即便是房租相同的条件下,黑人租户的居住条件往往更加恶劣。

小河成为了鲜明的种族居住界线。一些当地人曾冷嘲热讽说,河上的桥是世界上最长的桥,因为它连接着波兰和非洲。但是,河的两边却因为极端的贫困而具备着非常多的相同点:几乎无法忍受的卫生和安全条件;泛滥的吸毒、贩毒、卖淫、暴力等非法活动;房东、毒贩子和高利贷主的无限商机;还有显著的性别不平等。当然,如书中所表明的那样,种族和性别困境是交织的。黑人女性是最容易遭到驱逐的群体,而这种现象和黑人男性的高失业率和监禁率也息息相关(“Black men are locked in. Black women are locked out”:黑人男性被关进去,黑人女性被赶出来):由于孩子的父亲在监狱,单身的黑人母亲不得不只身面对贫困、歧视、住房和养育孩子等一系列的艰难困苦;而她们的儿子也往往会重蹈父亲的覆辙,女儿也很容易很早就成为单身母亲,这使得他们更加难以租房,摆脱贫困。同时,白人女性和黑人女性的共性在于,在收到驱逐通知以后,与男性租户相比,她们很难直接与房东进行交涉,而是会采取一些被动应对措施,比如向亲友和社会组织寻求帮助。男性租户则往往会直接与房东互动,采取协商、对峙、威胁或者以廉价劳动部分兑租的方式增加保住自己住处的机会。然而,即便是这样的努力,往往也是杯水车薪。租户Lamar,一个退伍军人,一个月的收入是628美元,房租是550美元。这意味着他每天能够担负的开销只有2.19美元。在他得知房东Sherrena想要把他赶走以后,他提出帮房东给房子刷漆,以此换取250美元的房租减免。但对于一个在流落街头时冻伤双腿而截肢的人来说,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他在儿子和邻居的帮助下爬来爬去,几天以后终于完成了刷漆的工作,却只了获得50美元的报酬。
被驱逐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拖欠房租是最主要的因素。这些挣扎在贫困线上的租户,不论他们的收入来源是什么——卖命赚来的工资、政府的福利还是社会与亲友的救济——在交完一个月的房租以后,往往每天只有一到两美元的可支配收入。这连基本的食物都买不起,更不必说其他的生活必需品了。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有的租户由于亲人过世去参加葬礼而开始拖欠房租;有的因为自己的健康问题而拖欠;甚至有因为去飓风受灾区做志愿者的交通费用而开始拖欠。而由于他们整体的经济状况本就十分艰难,一旦进入拖欠状态,便十分难以从中脱身。这种情况下,被驱逐便是只一个时间的问题。

政府、法院、教堂、警局、监狱、戒毒所与搬家公司:组织的深渊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即将面临或者已经被驱逐的住户,在他们所接触的形形色色的社会机构面前,只有两个身份:被救济的对象和被惩罚的对象。联邦层面政治的潮汐、各州的社会政策风向、地方层面基层公务员的决策和社会福利机构的容纳能力,都强力摇摆着每个穷人的命运,具体地决定着他们下半月能不能吃上饭、今年是否得以在室内过冬。90年代,本地保守派政治家在Milwaukee进行的福利紧缩政策,使得两万两千个家庭丧失了保护。与此同时,国家通过了克林顿政府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的法案,这些改变影响至今。由于地方和联邦政府提供的资源远远无法保障贫苦租户的日常所需,因此他们必须依赖其他社会救助机构。书中人物之一Larraine在收到驱逐令以后,打了所有自己能想到的机构的电话,但都没能接通。她尝试去求助了自己常去的教堂,但牧师也十分为难。在城市的另一边,黑人贫困区的孩子们也早就习惯了每周两次在窗口守候教堂发免费午餐的巴士。贫困区长大的孩子们习以为常的,有驱逐经验丰富、手脚麻利的搬家公司,被搬家公司扔出去的满街的衣物和日用品,还有警察和监狱。租户Lamar与他儿子打牌时曾经闲聊如何同警察打交道。而他们的房东Sherrena除了收租,也开辟了一项新的业务:向贫民区的租户以25到50美元的价格提供去监狱的往返交通服务,以方便这些人去探望被关押的亲属。
平民,特别是穷困人口与官僚机构的互动,是西方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里一个广泛关注的话题。从80年代的里程碑作品《基层官僚》(Street-Level Bureaucracy)到最近的《官僚与穷人》(The Bureaucrat and the Poor),近40年来,欧美新老学者深入研究了老百姓与福利办公室官员、移民官、警察、医生、律师的直接接触。这些从业人员对平民的生活有着一线的决定权。而在这样的互动中,平民在有限的资源和制度空间里争取和放弃着与自己的生存息息相关的种种权利。这一领域的一些洞见——例如弱势群体在基层官僚中的的失语、悲观和对他们的不信任——也在本书中获得了印证。要出庭才能获取正式的驱逐手续,但是往往只有房东在法庭出现。被驱逐的租户要么早已放弃争取的机会,要么因为交通成本和不得不保住的工作而无法出席。而出庭了的租户对法庭和法官的感受则是负面和手足无措的:严肃而陌生的环境里充满了绝望的老弱病残,到处跑的孩子和轻车熟路的房东。各种杂乱的对话,时不时被连续三个盖章的声响打断。

他们在医疗矫正机构中也有相似的经历:Scott,一位曾经的执业护士,因为常年繁重的工作而受背伤后,逐渐产生了药物依赖,最终被吊销执照,流落街头,并接触到了海洛因。在接踵而来的绝境之后,他下定决心去戒毒。他天没亮就起床,刮胡子换了像样的衣服,去戒毒所排队。开门后,站在几十个人队伍里的他被告知这里一天只收留五个病人。当叫号的人喊到2的时候,他离开了戒毒所,回到了毒贩朋友和海洛因的怀抱。
房东、家人、朋友与爱人:关系的朝夕
Desmond在书中说,他做这个研究的初衷之一是认为贫穷是一种关系(“Poverty was a relationship, I thought”)。这一系列社会关系里,有上文提到的贫困人口与社会机构的关系,也有近距离的私人关系。经济的拮据、资源的匮乏、不断变换的住处和各种难以启齿的往事与现状,考验、阻碍、瓦解和形成着这些关系。这些不同的过程,虽然因缘结局各异,走心和复杂程度也不尽相同,却都转瞬即逝。
房东与租户之间的关系是驱逐的核心。他们之间既存在着利益的关系,也有相互的理解和对彼此的厌恶。房东为了保证收租及房屋不受破坏,需要了解租户人生的点点滴滴。在这个过程中,精明的房东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商机,进而发展出了一套管理和收租技能。但在相处之中,他们难免也会产生一些怜悯之情。租户有时会从房东那里获得食物、房租的延期和交通上的帮助。但说不准不久以后,房东就用一道驱逐令把他们赶出门外,房东也可能全副武装,用真枪实弹骚扰他们。那些曾经为了凑齐房租愿意出力为房东干活的贫穷住客,现在则会破坏房屋来进行报复。

在遭遇驱逐这样的危急时刻,向亲人求助从来不是贫困租户的第一选择。他们有的因为害怕难堪而向亲人隐瞒了自己的实际处境;有的考虑到没准将来还会有更加绝望的时刻,而不敢轻易动用这最后的稻草;也有些人的亲人与自己一样朝不保夕。此时,他们往往依靠脆弱却同病相怜的友情或者男女关系勉强维生:在将东西搬进付费储藏室的时候,被驱逐的Arleen认识了新的男朋友;Pam和Ned被从自己的活动房里驱逐以后,住进了Scott和Teddy的活动房。然而这样的关系不仅短暂,还往往雪上加霜:房东得知Scott和Teddy接收了Pam和Ned以后,对前者也下了驱逐令;Arleen和Crystal在公车上相遇后马上成为互相帮助的室友,最后却一起被房东清出门。
参与者的温存与旁观者的冷眼:一场尴尬的博弈
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对自己的角色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自觉。在书中,他讨论了自己的性别、种族和阶级对他的研究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强调说,“我”(I)不重要,并呼吁读者多看到Larraine, Lamar, Arleen和Scott这些故事真正的主人。
确实,全书从整体来看,特别是与他上一本著作相比,能够很明显看到他将自己抽离出来的努力:正文材料里没有任何研究对象与作者直接的互动,也没有与他的在场相关的表示,甚至在他确实参与和产生影响的情况下,作者也以“朋友”而不是“我”来指涉自己(见本书后记)。但是,“我”在某些地方还是欲盖弥彰地表现了出来。本书第18章“食物券买的龙虾”(Lobster on Food Stamps)里,他尝试去理解和解释为什么Larraine这样的穷人在发救济了以后,会把一个月不到一百美元的食物券用来买龙虾这种比较昂贵的食物(龙虾一磅价格一般在10美元以上),却没有精打细算合理消费。在他对这一现象进行问题化的过程里,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尴尬的张力:作者借用了主人公Larraine周围的人——前文从未提及的一个外甥女,和提到过一次的牧师——对她的评价来对她的消费行为提出疑问,而这两个人无疑都把她的这种行为归结为她自己的错误思维。当Larraine询问作者为何如此感兴趣于研究她的食物消费时,他以未来读者也许会表示疑问作为理由解释了自己的疑问,以研究者的身份保护了自己,并且代表了这些不在场不可见的未来的读者继续向她发出了一系列的追问。
而Desmond也坦承到,田野工作令他感到负罪,伤心越绝,抑郁数年。他在日记里写到:“我像收集战利品一样收集这些故事和困境,这让我觉得肮脏。”他在田野里帮助过他的研究对象解决困难;田野结束以后,有时也会寄钱过去,帮他们交房租和保释金。而租户们把他当朋友来保护与看待,给他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有一次,与Lamar同住的Hinkston一家人让Desmond到他们地下室帮忙拍几下不好使的锅炉,当他无功而返时,发现这一家人给他准备了一个生日蛋糕;Arleen给他买过一罐饼干和一张打开以后会播放音乐的卡片,他们在心情不好时,会把卡片打开一起笑一笑。Scott在多次尝试戒毒以后,终于成功,并开始了新的人生,也有了新的住处,而他依旧会像曾经无家可归的时候一样,给Desmond的大儿子寄生日卡片并在里面塞10美元的纸币。
在书中这些地方,我们再次看到了《在火线》里那个走心的、为每一个研究对象读和他们有关的段落的初出茅庐的小伙子。而与《在火线》末尾一样,Desmond十分具体、直白地提出了政策建议。他指出,这些政策改变迫在眉睫,因为现在每五个美国家庭里,就有一个把收入的一半花在房租上。他提出,政府首先需要从司法机关下手,向低收入家庭提供法律援助,特别是专业律师的服务。同时,负责驱逐案件的民事法院也需要获得更多的资金,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对市民进行服务。
另外,他提出当前租赁市场存在严重的剥削现象,特别是房东和租户之间的剥削关系。而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最低工资和基本社会保障,对于抵抗剥削,改善租户处境,降低驱逐的发生频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同时呼吁全国性的公共住房券系统(housing voucher program)。这种措施与前文提到的食物券有类似之处,但目前只在部分地区使用,也只有210万美国人受益;而Desmond表示,这一举措可以普遍地推行。收入低于某一水平的家庭可以申领住房券,一家一张,他们将收入的30%用于房租,其他用住房券作支付。他们能够使用住房券的住房总价格和条件根据一系列的算法决定。这样的住房措施会使低收入家庭在住房市场上获得保障。
田野工作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与距离,与其他一切关系与距离一样,是一种双向决定的、与具体的时空情境息息相关的无休止的平衡与抉择。研究者可以选择一种更为亲切的长期的互动和关怀,而也可以把自己与眼中的社会工作者和义务服务者等等划清分工界限,为自己武装上可观察又能隔离的屏保。在Desmond这一部作品里,我们看到了一种有意无意的矛盾,这是一种真诚的关怀和充满戒备的掩饰的混合。
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贫困:他们的不幸与你我有关
最后,这本书将贫困作为一种关系来看待,这种视角可以也必须应用于学术界和研究者本身:贫困作为一种关系,也将作为学者的我们纳入其中。社会研究者和媒体人,对这些缺乏基本生存和权益保障的个体的人生有可能产生十分具体的改变和影响。但同时,他们也造就了我们。

因此,这些在食物链底端的朝不保夕的无助之人,不仅成就了毒贩子、高利贷、房东和搬家公司,也成就了许许多多的媒体人和研究者。学术界和学术研究者是不平等的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他们也从弱势群体的苦难中获益:研究成果、教职职称和各种荣誉,这些利益琐碎却又真实。作为最缺乏资源和保护的群体,贫困人口对我们的知识生产的奉献是最为原始、痛苦和巨大的。因此,他们值得我们以最大的恭敬、真诚和责任去面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