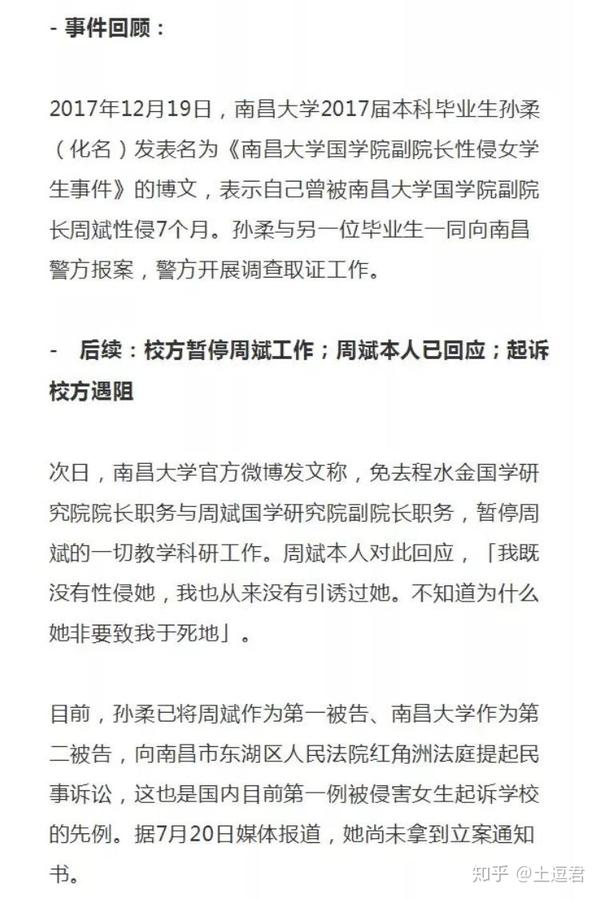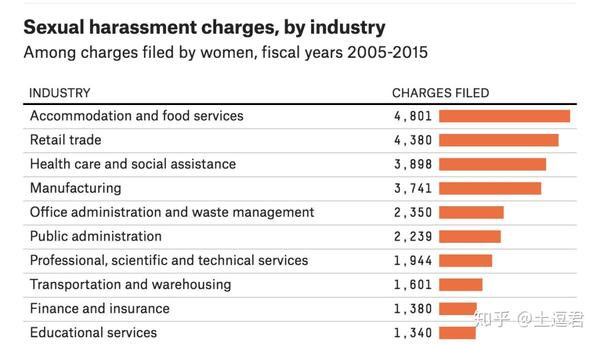(写在前面:台湾的原住民不是汉人,而是南岛民族,今天自称台湾人的汉人,根本就是入侵者的后代,他们无耻的侵吞原住民的土地,指责原住民“落后野蛮”,又无耻的拿原住民装点门面。)
文/王嵩山
概說
正如同地理環境的變化多端,在人文上,臺灣是一個多元文化並存發展的島嶼。除了三百餘年前移民自中國大陸閩、粵為主的漢民族,臺灣更有為數約四十五萬人口的原住民族,分佈在三十個山地鄉和二十六個平地鄉鎮;此外,也包括與漢文化互相影響的平埔諸族。
臺灣原住民早期居住在中國之「邊疆」,被視為文化水準低落、信仰與行為不合理性原則的「非漢民族」。從有歷史記載以來,臺灣原住民族在文獻和地方志上通常被稱為「東鯷」或「東番」。有清一代,則根據土著「漢化的程度」,稱呼他們為「東番」、「野番」、「生番」、「化番」、「熟番」。日據時期,臺灣土著被稱為「番族」或「高砂族」。光復後,行政上土著族被統稱為山胞,並區分為「山地山胞」與「平地山胞」。至於學術上對臺灣原住民族的稱呼,則有「土著族」、「高山族」、「南島語族」等用法。在主觀的認知上,這些族群較願意分別的被稱為達悟、泰雅、布農、賽夏、鄒、阿美、卑南、排灣、魯凱。
事實上,這些名稱的意思多半指的是「人」。近十餘年來,原住民運動團體辛苦爭取到的「臺灣原住民」之統稱,成為確定「人族」之主體性的象徵。
雖然臺灣原住民族在社會文化上都屬於馬來 / 玻里尼西亞系統,但是彼此之間仍存在很大的差距。比方說:在政治體系上,從平權的達悟、布農社會到有貴族與平民之分的魯凱、排灣階層社會;在宗教上,從不具特定型態的精靈信仰到多神信仰;親屬組織則不但存在著偏重父系或母系的單系親屬群,也可以看到雙系親屬群的型態。臺灣十幾個「人族」,呈現多面貌、多樣化的社會文化現象。
不僅如此,雖然現在我們對於臺灣原住民族歷史的認識越來越多,不過大致是編年紀事式的條列歷史,較難顯示以原住民文化為主體的認識。本文提出一個例子,目的在說明從史前到近代原住民歷史其實是由其個別的社會文化的性質界定的,不論是著名的阿里山鄒族的吳鳳事件,或是南投泰雅族的霧社事件,都與既有的社會文化產生緊密的互動。
變動的世界:起源、記憶與歷史
原住民族的社會一直在轉變中。不但有內在的調整之動力,也與外在的影響因素互相關聯。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民族國家興起,一九六○年代的個人主義,以迄一九八○年代重視差異、重視少數或弱勢的聲音(如原住民和非歷史主流的地方史)、強調多樣性(以及進一步的衍生出物種保護主義與生態主義)等歷史趨勢,繁衍出當前世界最複雜的事務:宗教狂熱與族群意識勃興的現象,這二種現象都屬於文化形式的範疇。臺灣當代原住民社會文化的發展,也在這個歷史脈絡裡面。
造成原住民社會轉變的力量,來自工技或生態的物質面相、社會組織或制度、思想或信仰等三方面的外在介入或內在變動。
臺彎原住民族群自十九世紀末以來,便已被納入國家社會的政經與文化脈絡、甚至世界體系之中。原非封閉式的、非無時間性的思維、與非整合的社會關係,更積極的與外來的社會文化體系對話。換言之,世界隨時在改變著,而原住民文化本身亦具有變動不居的性質。
一般認為華南或大陸東南亞是使用南島語系民族發源之地。考古學家以為臺灣的史前文化,與中國東南沿海古百越之地有密切的關係。臺灣位於目前南島民族分佈的西北方。位於文化交往要道的臺灣,來自於中國大陸華南、東南亞、與大洋洲南太平洋的文化在此聚合。
臺灣位於東亞大陸塊的邊緣部位、大陸與海洋地殼交接的地塊之上。距今約一萬年到三百萬年前,幾次冰河期曾引起世界性的海面下降;臺灣海峽某些大陸棚地段因此露出,使臺灣與中國大陸華南的陸地連成一體。正由於更新世期的臺灣與華南數次以陸地互相連結,使華南的哺乳類動物與舊石器時代的人類與文化,有可能過渡到臺灣來。近年來,在臺灣海峽所發現的遺物正支持上述的推論。
臺灣的史前文化遠較其歷史時期文化久遠且複雜。史前的遺跡與遺物,分佈遍及全島及周圍諸島。目前所發掘出來的器物,包括石器、玉器、陶器、骨角器、青銅器、鐵器,以及人骨遺留等,存在的年代遠自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到金石並用時代,分屬於不同時代的文化層。考古學家認為,從各個遺址的研究中顯示出不同的史前文化層,不但有臺灣獨有的器物,也有接近東南亞文化系統的器物。換言之,臺灣史前文化並非僅有單一來源。
民國五十八年元月間發掘的臺東縣八仙洞長濱文化,年代約距今 12000~15000年前左右,屬舊石器時代文化。發現於臺南縣左鎮菜寮溪中的左鎮人,也有兩萬年左右的斷代。新石器時代的臺灣,各具代表性的文化,此起彼落。比方說,在臺灣北部有大坌坑文化(約距今6500年~5000年)、圓山文化(約距今3500年~2500年)和十三行文化(凱達格蘭文化,約距今900~1500年)。在東部則有麒麟文化(或稱巨石文化)(約距今3500年~2500年)、卑南文化(約距今3500年~2500年)。
目前我們雖然無法明確的認定這些遺物與臺灣現存原住民之間的關係,但是在原住民中,北部和中部各族與大陸東南海岸的文化有關,南部與東海岸各族與南洋群島文化有關,則被認為是可以接受的。當然,史前文化並非全部是原住民祖先的遺物,例如,大部分在西海岸所發現的新石器時代後期文化與臺灣原住民文化,尚無重要關連;而東部巨石文化與現今的阿美文化間,也沒有承繼關係。
遠在距今五、六千年前,與現存原住民族群有直接的血緣關係的民族,先後、陸續的由華南或東南亞移居到臺灣島,之後又遷徙擴散到大洋洲群島。在族群的學術分類上,這些現存約四十萬人口,包括達悟(雅美)、泰雅、布農、賽夏、鄒、阿美、卑南、排灣、魯凱、邵等族群。而被認為與漢文化互相涵化的平埔諸族,也應該是原住民族群的一員。由於這些早期臺灣的住民都使用南島語言,在人類學的學術用語上便統稱為「南島語族」( Austronesian)-活躍在亞洲大陸南方島嶼群上、屬於同一個語系的諸族群。
南島語族擁有強旺的活動能力。在地理的分佈上,東起南美洲西岸的復活島、西抵非洲東岸的馬達加斯加島、南到紐西蘭為止的印度洋至太平洋的廣大海域,都是使用南島語的民族居住與活動的地方。臺灣則位於目前南島語族分佈的最北方。
無論如何,與漢人大不相同的起源、記憶與歷史,配合傳統神話、信仰、儀式與物質文化,已成原住民族的精英份子建構當前社會生活的依據之一。
臺灣原住民族社會文化大綱
根據語言的分類,臺灣南島語族又可分為三群:泰雅群( Atayalic)、鄒群( Tsouic)和排灣群(Paiwanic )。三群之內因文化之間的交流與地域化而產生差異。泰雅群又分:泰雅、賽德克二方言系統;鄒群分阿里山鄒、卡那布、沙阿魯阿三方言系統;排灣群則分為魯凱、排灣、卑南、布農、阿美、達悟(雅美)等方言系統。
語言現象使目前臺灣原住民族群的分類更形複雜;比方說,有許多使用賽德克語的太魯閣人,便認為自己是「太魯閣族」,而不是「泰雅族」。不論如何,各族彼此之間的語言與馬來語有其密切關係。十二個臺灣南島語族,又可分為平權的社會(雅美、泰雅、布農、太魯閣)與階層化的社會(鄒、排灣、魯凱、卑南、阿美、邵族、噶瑪蘭)。
雅美(達悟)族分佈在太平洋的蘭嶼島上,其居處方式是定居的,家屋毗鄰而建,構成集中型的村落,村落中的政治範圍是以父系世系群為基礎,而表現在水渠灌溉系統和漁團組織上。傳統的雅美(達悟)人,主要生產方式有二︰一種是以水田定耕與山田耨耕的農業,另一種是海上捕魚。山羊放牧與豬雞等家禽、家畜的飼養及野生植物的採集,是普遍的次要生產方式。在工藝技術方面,雅美(達悟)人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家庭手工藝社會,一切基本器用、衣服及著名的漁船,都是靠自己的技術和原料製造。由於雅美(達悟)是典型的島民,其宗教信仰不但與社會整合有密切關係,也與捕魚生業密切關連。政治權力普化在社會結構的各個層面上而未集中化。
泰雅族和其他臺灣原住民族一樣是以農業為主要的生產方式,原有傳統的農耕方法為山田燒墾,所種植之作物以穀類(如粟、陸稻)較塊根類(如甘薯及芋頭)為多。次於農業的生產方式為狩獵,方法有陷機獵、個人獵以及團體圍獵。團體圍獵行於夏秋乾季,常有宗教意義。泰雅族男人為著名的獵者,女人則善於織衣。其親屬組織主要是以個人為中心的雙系團體,單系親族的組織原則較為鬆懈,泰雅人轉而借重另一個共同祭祀的嘎嘎( gaga )團體為基礎。基於祖靈信仰的嘎嘎(gaga )是整合社會的重要因素,而且這種信仰更因其在經濟或農業技術上得到的支持而更形加強,成為一種維持社會秩序的支配性價值。泰雅族的各類領導權,因後天成就而獲得,權威亦未集中化。
傳統的布農族,經濟完全依賴山田燒墾的生產方式和打獵而來,勞力並不被某一特定的社會群體所控制,家庭勞力由家內人口、家外人口與姻親組成,而在開墾的階段,則以地緣為基礎組成換工團體以獲得勞力。土地只是勞力的運作工具,為家庭及其後代所有;家庭的山田燒墾,是一個自足的經濟體系。生產因素及財富並未形成累積的現象,直接提供布農族人權力普化的基礎,此又因布農人強調個人的能力以其在團體活動中的表現來認定、社會組織呈現多樣性、組織團體小而趨於分裂等三個結構原則之運作而更加強,造成社會成員對社會資源的取得有平等的權利,而且領袖也較不能獨有某些利益。這些情形也見之於宗教上未有神的系統,而以精靈信仰為主的現象。
賽夏族之住居,家屋二、三家成一小聚落,為散居之村落。父系氏族為部落組織之基本單位,然而氏族並非集中居住,每一氏族所包含之家族單位,零散分佈於各部落屬下之各村落。賽夏族人行從夫居制,在繼承方面多半是長子、次子逐次外分,而由幼子繼承家屋。家屋中的內部設備,最主要且具有神聖意義者乃是祖靈袋,祖靈袋只限於氏族宗家才有,由宗家的家長當司祭。各部落或部落同盟間,若干重要祭儀的司祭權,經由世襲而分屬於各主要氏族。矮靈祭是全族性的祭儀活動,通常在粟收穫後,稻已成熟而未收穫前之間舉行,並每隔一年舉行一次。賽夏族的權威逐漸由個人轉向特定的世系群,並在宗教信仰基礎上結合地緣關係來運作,出現初步的世襲現象。
鄒族為一父系社會,行山田燒墾,以小米和甘藷等為主食,而以獸肉、魚類為輔。土地為部落或氏族所有,個人只有使用權,除了簡單工具之外,生產均依賴人力。生產的主要目的在於自用,除了自己生產所得與共享性的分配所得之外,餽贈及物物交易是得到非自產必須品的另一種方式。鄒族之基本社會單位與經濟單位為聯合家族,部落組織分大社和小社,整個社會由頭目、軍事領袖和巫師所控制。傳統的鄒族社會在結構上呈現出一個主要中心周圍環繞數個小旁支,中心與旁支彼此有明顯的高低階序關係的特徵。這種結構原則,不但在傳統的山田燒墾和漁獵的經濟過程中得到支持,同時更透過父系氏族的親屬聯結、男子會所與年齡組織的運作,以及對部落首長所代表的整體部落價值的輸誠效忠,而得到其整合和延續。
居住在臺灣東海岸的阿美族雖是母系社會,但是其政治體系的主要基礎乃在於男子的年齡組織上,而非在母系氏族或世系群。阿美族的聚落形態以定居、集中、幅員廣大為其最明顯的特徵;其主要成因乃在於行刀耕火種與水田稻作的生產方式,以及防備平原北部的泰雅族與南部的布農族之威脅這二個因素所影響而形成的。阿美族行從母居,財產和家系的傳承都是母女相承為主,親屬體系中單系組織有嚴整的階層關係,這種階層關係也呈現在宗教信仰方面龐大的神祇系統,甚至其巫師也自成一個階梯次序。領袖制度和年齡級制是阿美族政治的兩大基本要素,在這兩個基本要素之中,也呈現出社會結構之階序原則、組織之專門化與特化的現象。
從日據時期到現代,卑南族以農業為主要生產方式,以飼養為輔,狩獵則僅因個人的興趣及為傳統儀式所需而從事。農業型態同時並存著水田和旱田兩種耕作系統,水田作物約在距今九十年以前傳入,旱田的耕種則自古即有,作物以小米、陸稻、高粱、芝麻、樹豆、甘藷、玉米為主。這種定耕、定居、飼養的經濟型態,配合強有力的部落組織與會所制度、年齡階級制,使得卑南族曾有一度顯示其在東海岸強大的擴張力。共同的姓氏和祖家祭祀象徵世系群關係範疇,家庭中的家長雖由女嗣繼承,但宗族的首長和司祭則由男嗣繼承,男子即使出贅並不影響其成為母族的氏族首長和司祭的機會。部落內公共事務透過會所制度和年齡組織所整合推動。
魯凱族從事山田燒墾,並以狩獵、採集、捕魚為副業,每一社區之土地屬於幾家地主貴族所有,直接從事生產工作者為無土地權的平民,其生產所得必須向貴族家繳付租稅。魯凱人以家宅、家氏為親族關係發展之基本要素,並施行偏重父系的雙系繼嗣法則,每一家宅原則上由長子承居,無男嗣時由長女承家居住、餘嗣分出。直系承家繼續其家氏,旁系分出之後,自立為分家之家氏單位,而與其家維持系統的階序關係。部落中之祭儀、行政等事務均由頭人階級所掌握指揮,他們的服飾及家屋雕刻也大別於一般平民,而成為貴族地位的象徵物。階級性的社會和財富的累積以及分工的專門化,使得魯凱族的工藝,尤其是木、石雕刻,發展出特殊的成就。
生計方式在排灣族是以山田燒墾為主,兼事狩獵、山溪捕魚和畜養。生產的目的是自用,一部份則作為繳付給貴族的租稅。狩獵與捕魚都需向貴族繳租稅,貴族則可給予平民若干報酬,使平民去做公共或貴族私人之事。排灣族的繼嗣法則為長嗣繼承、餘嗣分出。家是一個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社會單位,家庭成員、家名、家屋所在地、家系地位、特權等整個結合成為一個叢結。宗支系統乃由家宅系統發展而成,並且有直系中心,愈接近直系的,其家系地位愈高,因此形成階級化的貴族宗支組織。如同魯凱族,排灣族的工藝也在財富及貴族制度和神話傳說的基礎上,展現極其豐饒的創造力。
十七世紀的臺灣南島語族版圖
十七世紀以前,南島語族構築臺灣的族群版圖。雖然,臺灣史前文化與目前原住民之關係的圖像,尚未完整且細膩的勾勒出來。但我們已經明確的知道,史前文化的主人和南島語族,在不同的時間、分批進入臺灣。認為現存原住民族分批進入臺灣的論者,相信這次的遷移最早可能在西元前三千年至四千年左右,也就是距今約五千年至六千年。
分佈在臺灣北部的泰雅族與賽夏族沒有發展出陶器工藝,以善於黥面、巧工織布著稱,這兩個族群到達臺灣的時間最早,約在五千年至六千年前。中部的邵族、布農族、鄒族約於三千餘年前到臺灣。在南部與東南部發展出階級社會、藝術成就極為發達的排灣族、魯凱族和卑南族,約在一千餘年前到達臺灣。東臺灣的阿美族文化與菲律賓金屬器文化相似,約在公元後到臺。達悟族,則一直要到宋時期,才由菲律賓遷徙至孤懸於太平洋中的蘭嶼島上定居。
三百多年前,閩、粵的漢族大量移民臺灣。其時,臺灣西岸的平原,尚有大量平埔族定居,逐漸地受到強勢漢文化的影響。到十九世紀末,可辨認的平埔族,尚有:分佈於基隆淡水海岸地區及一部份居於宜蘭縣境的凱達格蘭族,居住於臺北盆地及其周圍的雷朗族,宜蘭縣的噶瑪蘭族,分佈於新竹、苗栗二縣的海岸平地的道卡斯族,臺中縣境有巴則海族和拍瀑拉族,巴布薩族分佈於彰化縣境,和安雅族居於嘉義與南投二縣,西拉雅的三個亞族分佈於臺南、高雄和屏東三縣,馬卡道分佈於高雄一帶。以日月潭為生活中心的邵族,有時也被歸入平埔族群。
臺灣的南島語族不只以其特殊的社會文化體系,適應於臺灣的生態環境,也遭遇外來的政治、經濟、宗教力量的影響,在傳統的持續與激烈的變遷之夾縫中求生存。一般而言,臺灣原住民族的社會文化體系經歷了四個演變階段,由於社會文化體系與外來影響互動,文化體系與社會體系有不同層次的整合。
這四個階段,一是傳統部落生活。二為荷、清時代,建立外來影響的基礎,開始被捲入現代世界體系。接著歷經五十一年的日本殖民政府的間接統治,更進一步的與世界的政治經濟及宗教的體系互動。最後進入國民政府的治理時期,西方的科層制及外在政治、經濟、宗教等體系,加深擴大其影響力,再加上臺灣當前政治與意識型態之左右,不同文化建構出多樣化的歷史。
這四個階段之社會文化變遷所產生的適應問題各不相同、性質迥異。在傳統部落由既定的血緣、地緣及各類身份地位形成法則所交織而成的社會生活中,變遷是較緩慢的,而社會文化體系也自然形成自成一格的適應機制,以避免在過激的變動之中,導致社會文化體系的崩潰瓦解。反之,在遭受到大社會的強大外來文化之衝擊時,往往抵擋不了種種壓迫與剝削,從而在內在產生無法適應的狀況。而且這些適應,又因社會文化的不同,而在政治、宗教、親屬、經濟等方面的表現都有所差異。例如,階層化的社會傾向於信仰天主教、政治選舉較易連選連任,平權化的社會則傾向於信仰基督教長老會、政治選舉不易連選連任。
文化與歷史:一個人、兩種文化、三段歷史
遙遠的一七六九年,吳鳳成為過去。一個人捲入兩種文化造成三段歷史。
出生在大陸的吳鳳,五歲隨父母來臺。鳳父常與阿里山鄒人進行貿易,又兼開墾事業,吳鳳因此常隨父出入阿里山鄒人之地,了解鄒人的語言與習俗。自康熙六十一年( 1722)起,吳鳳任通事,管轄阿里山鄒人的番課、漢番之間貿易以及漢人移墾事宜。吳鳳擔任通事長達四十八年之後死於沙米其的鄒人之手。
鄒人為何殺吳鳳呢?起因與通事執行職務有關。通事是安撫生番之人選,負責管理山產交易、輸餉事宜。清代的通事也有由土著擔任者,因此其本身也可能擁有租戶的身分,可將田地給人開墾、收取田租。正因為通事統籌土著日常生活事務,所以不良的通事就會剝削土著。康熙收臺灣不久,高拱乾來臺視事,要求官兵、通事等人「不准勒索土番、苦役生番」,但前述情形持續發生;漸漸地,通事更成為土著事務的操縱者。
由於土著不懂漢文,故常有通事「假課餉之名、行侵占番地之實」。康熙五十八年( 1719)一張以阿里山生番為名訂定的契約中,便顯示當時阿里山的頭目之一Avai ,因為社餉非常繁重,不得已將土地交付給吳鳳去「招佃」,約定每年須納榖三十石,以補貼阿里山社該交之「社餉」。1768年起,又要對番社另徵小米,每石折銀六錢。當時土著將鹿皮及小米交由社商包辦,社商也趁此機會剝削番社。通事、社商、夥長、官兵聯合剝削。他們使役男人、婦女與小孩;賣生番、娶納番婦更比比皆是。
正因為難以容忍的剝削,導致「生番殺通事」情事。康熙六十年( 1721)朱一貴之亂,阿里山及水沙連各社趁隙殺通事。諸羅縣邑令孫魯多方招徠,一方面示以兵威火炮,另一方面賞予煙、布、銀牌等物。歷經年餘,阿里山各社的頭目Mo’o 與水沙連社南港的頭目阿籠「就撫」。這一年,吳鳳就任通事。
鄒的集體記憶是如此書寫的:由於作為通事者的吳鳳,對鄒人不當的交易與剝削而造成報復性的殺戮。吳鳳死後,嘉南平原及山區惡疾流行不斷,鄒人大量死亡、產生極大的恐懼。素有巫術信仰的鄒人,認為巫師無法治療的兇猛疾疫,無疑是吳鳳之靈所帶來的。鄒人不敢到漢人領域(也就是漢人史書中的「中路以西」)獵頭。雖然如此,自沈葆楨「開山撫番」至日據初期一九一○年左右,阿里山鄒人因爭取、保護其自然資源而出草獵頭的事件從未間斷。
至於平民漢人的地方歷史,通事的惡行惡狀自然不見書寫。吳鳳之死不但庇蔭了「中路以西」的居民免受鄒人威脅,也扮演弭除天花等惡疫角色;相信受其「保護」的漢人,根據其民間信仰,將吳鳳神格化為「吳鳳公」和「阿里山忠王」,成為臺灣厲神「王爺信仰」的新成員,被供奉在廟宇與家中,相信他會「保境安(閩南)民」。吳鳳信仰建構出和鄒的族群界線。
日據時代的殖民政府,政治的需求滲入歷史書寫,吳鳳被塑造為「成仁取義」的形象。一九○四年,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撰碑紀錄吳鳳行誼,而曾經大力鎮壓原住民的總督佐久間,也親頒「殺身成仁」匾額,既創造一段神話、也建構泛原住民族的野蠻污名。二次戰後,吳鳳更成為當時臺灣省政府極力讚揚的「公務員表率」,研議以他的誕辰為「公務員日」,蔣中正親頒「舍生取義」匾額。官方的吳鳳事蹟,也被編入小學課文之中。
一九八○年代的臺灣,挑戰「吳鳳神話」運動成為原住民族解構殖民統治與消除野蠻污名的里程碑。嘉義市火車站前與森林遊樂區的吳鳳銅像被推倒,吳鳳的故事從國小課本裡取消,吳鳳鄉改名為阿里山鄉。但是,過去既然是一種社會文化建構,與信仰和政治相連結的歷史,是不是從此就單純化了呢?
目前,除了名聞遐邇的三級古蹟吳鳳廟積極整修之外,阿里山公路由石桌轉進樂野部落之前,山頭矗立一座供奉著吳鳳的「忠王廟」;每年,吳鳳誕辰,漢鄒邊界處處上演「忠王」的祝壽、進香、民藝展演事宜。電視臺全程轉播「忠王廟」的「安座儀式」,依然以漢人的觀點強調他的「仁德風範」。而二○○二年的五月初,鄒人赫然發現吳鳳居然與前市長許世賢等三十六人,列名嘉義市的史蹟資料館「先賢錄」。吳鳳廟帶有濃厚的的鎮「番」意味,漢人的信仰雖然不能遽爾消除,那就想想吳鳳的其他文化價值,同時也應避免官方主導復辟具爭議性的歷史。